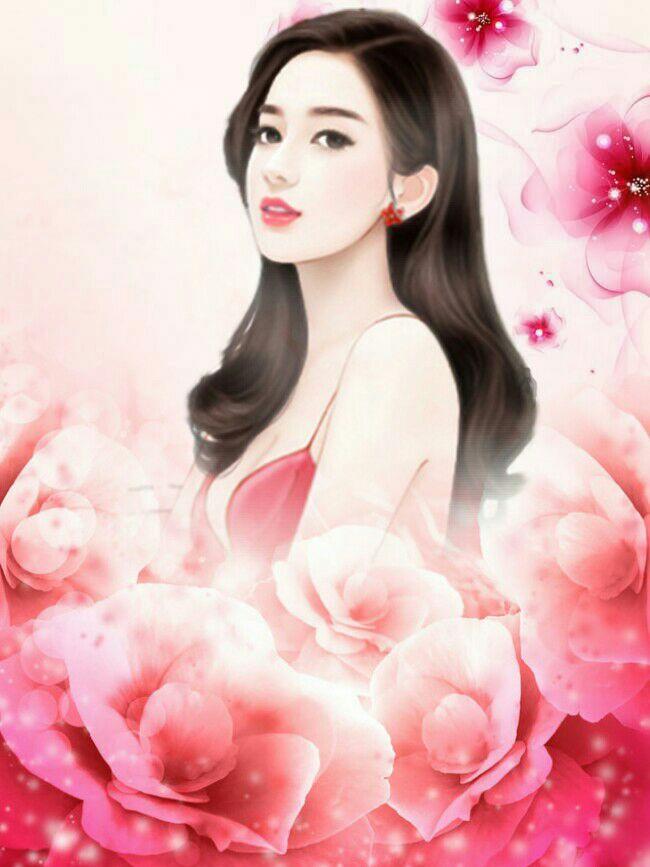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歧途:我一生的岔路 > 第七十七章 受人愚弄(第1页)
第七十七章 受人愚弄(第1页)
“我所说的……不,应该说是我的揣摩、揣测。”苟步仁纠正之后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揣摩他们的‘别有看法’,是不是他们在考虑其它问题。比如说,他们是不是考虑到你和金琬、共同犯过的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啊,担心让你们结婚了,会助长其他人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呀,会遗留后患呀等等方面的顾及。当然我这只是揣测、是猜想。”
卯生忽然被震惊得瞪大了眼睛。他觉得苟步仁将问题扯进了又一新领域,扯出了又一新问题。
这种说法与理论都是荒唐荒谬的。可是它在这特殊时期,在某一层次中,定会博得人的附和,定有很大响应力。这远比河马那“妨碍安定团结”之类的屁话顶用,更能站得住脚,叫得响。
想到此,卯生不禁无名火起,但他人却木呆呆的。因为苟步仁只是“比如说”,只是揣摩和猜想,其语言语气轻描淡写,态度和蔼可亲。这不仅让他又一次感受到了有火发不出来的滋味,而且一时哽得没有话说。
咳,但愿苟步仁的“比如说”,只是顺口一说的闲话吧。他想。
苟步仁起身添茶,卯生趁此机会想了想,他忽然冷笑一声说:
“假设,他们真有这种考虑,我——不认为他们的考虑有道理。即使他们很有道理,也不能据此而推翻婚姻自由、和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吧?”
苟步仁似乎一怔,添茶时茶杯里的水溢了出去。他转过身来,又异样地看了卯生一眼,尔后才颇具恭敬地递上茶杯。然后对卯生似笑未笑地一点头说:“我看也是。所以,你还是再去找找他们,该说的话都说一说,或许就没事了。”
卯生又为难道:“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懂法律,而且相互踢皮球。”
“踢皮球?怎么是这种工作态度呢。”苟步仁似乎不满地嘟哝了一句,然后稍停一下对卯生说:“如果是这样,你想想,要是你觉得大队介绍信实在难以到手,是不是由我帮你找找公社领导?”
卯生一愣:奇怪,这人怎么啦,求他帮忙他不干,不求他却倒主动起来了。不过管它呢,有人帮忙总是好事情。想到此,他有压抑不住的高兴,不由脱口而出道:“行吗?”
“不敢说行。”苟步仁认真地说,“不过,运气好的话,有领导一句话,一个决定,远比你刚才叫我开个条子管用吧?”
“太好了。”
简直是柳暗花明的心境。
“只是,你也不要太高兴。”苟步仁似乎是受卯生高兴的感染,居然又浅浅一笑,然后严肃道:“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把握。搞不好,还有可能更糟。”
还能糟到哪儿去呢?卯生心想:大不了又是一个非要大队介绍信,又是一个必须按“程序、手续”办事罢了。于是他很坦然而又很自信地说:
“领导毕竟是领导。我希望能够得到领导的帮助和解决。至少,领导也可以开导开导大队上那些错误做法吧。”
“这么说,你定了?”
“定了。”
“那就这样吧。”苟步文说着,顺手收拾起了放在桌上的,卯生和金琬的结婚申请书以及法院那份证明。“留下这些东西,抽到机会,我如实向领导反映一下情况。如果领导同意你们结婚,大队自然不敢、也没理由不给你们开示介绍信了。”
“拜托了。”卯生陪笑道,“请问,你准备向哪位领导反映?”
“自然是党委、政府呀。”
“党委、政府?”卯生一怔,“这点小事,还交党委、政府?”
苟步仁摆摆手,眼睛带有笑意地说:“现在办事都这样,某一个领导私下是不敢表什么态的。这也是党委和政府的办事原则嘛。不过这样不是更好吗,公社党委、政府的决定,生产大队能不服从?”
“可是……”
卯生欲言又止。迟疑中,他隐隐有种不安和担心,觉得对方有些小题大做,抑或糊弄或别有居心。但他不能肯定这些怀疑,这怀疑被一种莫大的希望冲击着,否定着。
没有法制的年代,河马之流违法行为只是屁大个事,令人投诉无门,有理说不清。事已至此,路已走到这一步,舍此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呢?何况,党委、政府,堂堂大公社级的党委、政府,其成员应有相当素质和水平,至少不会是河马之辈法盲、无赖,也不会是刘秃书记那等货色吧?他疑惑中抱有希望。
“你想说啥?”苟步仁问。
“噢,不说什么。”卯生说,“只想问,我什么时候来找你?”
“你听通知吧。党委、政府的决议是要通过基层传达的。”
苟步仁说后,很自然地问起楚天身体情况,语气中带有关怀和对楚天的敬仰。这或多或少让卯生有些舒坦感。最后,苟步仁端起茶杯。卯生知道这是送客。
回家后,卯生向金琬详细说了经过。说毕,两人都对苟步仁的帮忙寄着希望,同时心情又都很沉重。特别是卯生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挥之不去,却又理之不清。
“算了吧。”金琬说,“其实该想的你都想到了,大不了党委、政府中又是一群坚持‘程序、手续’的苟步仁而已。除此,还能‘不祥’到哪里去?何必这么苦思苦想的苦自己。”
卯生叹一声道:“只能等他们通知了。”
然而大出意外。十天后,刘球珠书记来到卯生家,他慎重其事地口头传达说:“公社党委、政府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为何卯生与何金琬不宜、不能结婚。现决定由大队支部做好男女双方的思想工作,并积极帮助各自另寻佳偶……”
严肃,神圣,还他妈的富有人情味哪!可是这叫什么事呀?一群狗屁胡话的荒唐官员,他们凌架法律,还堂而皇之打着党委、政府旗号擅作决议,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这下真完了。一个河马践踏国法尚无处申诉,何况堂堂一级党委政府?
当秃书记说到:此决定交由大队支部严格监督执行时,卯生猛然站起,他一把抓起桌上茶杯,叭一声砸在刘秃书记脚边,歇斯底里地大叫:
“你给我滚!”
卯生哭了。
他一连几天不敢、不忍去见金琬。他深深感到自己于苟步仁前太嫩,太幼稚。结果落得自送上门地受人愚弄,伸着脖子,高喊感谢地挨人一刀。
自己是一块被苟步仁出卖的,下了油锅的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