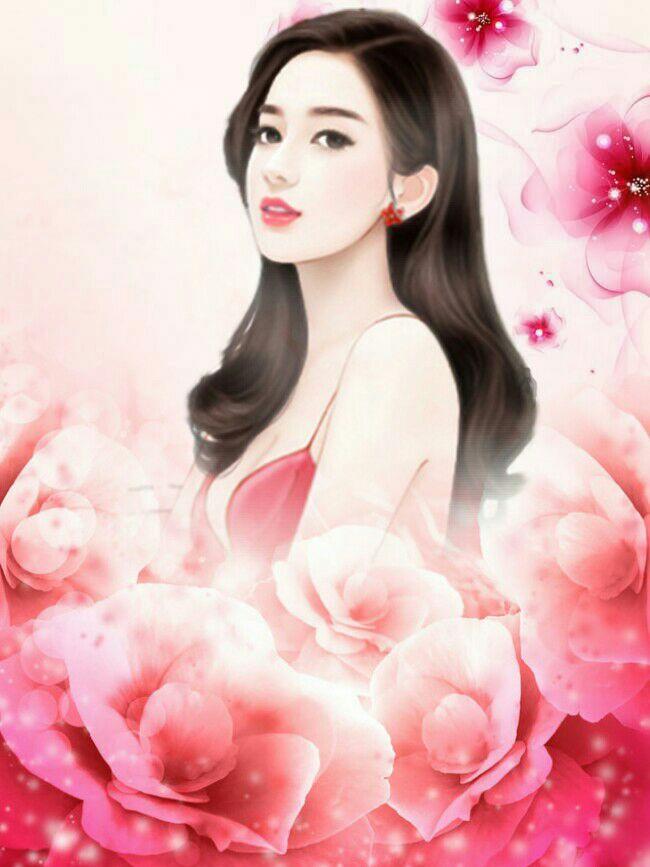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歧途:我一生的岔路 > 第五十三章 适得其反(第1页)
第五十三章 适得其反(第1页)
当卯生回到家时,父亲居然还坐着。如豆灯光下,他面容苍老,脸色阴郁而苍白。身旁一张小桌上放着饭和菜,一双筷子架在盖菜的碗蒂上。显然,父亲在等待儿子归来,等着儿子吃饭。
卯生突然感到一阵热血沸腾。他激动得拉起父亲的手说:
“我……到妈坟上去了。”
楚天似是艰难地点了一下头,说:“我猜你是去了哪儿。”
“伯伯,我对不起您。”
楚天缓缓抬起头,两眼望着儿子,两行昏浊的老泪夺眶而出。接着,他鼻子很响地抽动了两下,声音哽咽道:“儿啊……晓得了——就好。”
“可是我没有错,没有你们痛恨的那种错啊!”
卯生抓着父亲的双手,如泣如诉,迫不及待,一口气说出了金琬的真实身世。
开始,楚天如坠五里云雾。后来,他忧伤阴沉的脸慢慢缓和下来。但他似信非信,两眼紧盯着卯生的眼睛问:
“这是真的?”
“金琬说,她母亲结婚时,何贤岳接过您,您去晒田湾送过礼。您想想,那天是八月十五……金琬是第二年二月初二出生的,您算算,只有五个半月……”
卯生忽然停止述说,因为他发现父亲正在努力回忆。
不一会儿,楚天终于点头道:“嗯,不错,是八月十五,是打谷子的季节。我是同何贤海一路去的。”
“何贤海是谁?”
“何贤岳的大哥。”楚天又问,“那女子真是二月初二生的?”
“大活人,这还能有假吗?”
楚天想了想,像突然从烂泥坑中爬出来了一样,他很累很重地舒了一口气。他忽然伸出双手,同时按住跪着的儿子的双肩,带几分惊喜,又充满哀怨地问:“这些事,你咋不早说呢?”
见到父亲如此如释重负,卯生不由伤心而又欣喜地流出了眼泪。他如实说了为什么不能早说的原因,同时乞求父亲代人保密。
楚天猛听保密二字十分反感。直到卯生再三陈述厉害后,他才无奈地叹一声道:
“也是噢,闹出人命来,就更加麻烦,也是作孽呦。”但他不假思考,极力主张卯生立刻放弃金琬。
这大大出乎卯生意料。尽管他一再乞求父亲,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态度,楚天却依然坚决的,无情地加以反对。卯生终于忍无可忍,他忽地站起身来,用一种比父亲更坚决的口气说:
“不行!要我同她分手,除非我死了!”
“逆子!”
刚刚缓和的气氛又僵持住了。
好久,楚天才长叹一声道:“你娃子太糊涂呀。金琬不姓何,是另外一回事;人家现存要告你的可是破坏军婚,那才是更大的事情。你说是不?再说,世上的女人哪里就死净了,死得只剩一个金琬?啊!我咋就养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呦,啊!”
最后一个“啊”,父亲是带着哭音叫出来的,“喊”出来的。卯生心又软了。他重新坐到父亲身边,极力平静地说河马不仅是“要”告他,而是已经告了他。紧接,他详细说了金琬很早已经解除了婚约的前前后后。最后他强调地说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法律是尊重事实的,河马的无赖和诬告,注定是徒劳的。
楚天摇头。他说天下的理,理驳千层,层层都是理。又说官司是人做成的,不完全是凭道理打成的。卯生坚持说,事实胜于雄辩,有理就能走遍天下。
父亲又度长长地叹了一声。为劝醒儿子,他说古时候,有一乡绅说人世上的官司是人做成的,一穷秀才坚持说官司是据理打成的。于是乡绅趁秀才醉酒时做了手脚,然后说秀才入室行窃,有辱斯文,拉他上公堂。堂上,乡绅说秀才偷了他一枚铜钱,秀才自称身无分文,自己翻出所有衣袋,索要证据。最后,公差竟在秀才衣衫脚边夹缝中搜出了一枚铜钱。铁证如山,县官当堂打了秀才三十大板。
卯生说那是故事,是杜撰,不是真事不是现实。
如此,直到天亮,父子俩谁也没有说服谁。
楚天自从知道金琬不姓何,心理上确实得到了莫大宽慰,脸上的沉重少了许多,人也比过去精神了许多。但他仍有别样的担心,所以他答应过的保密事情,履行的并不彻底。
当他知道河马已经状告了卯生,老人诚惶诚恐,竟然找到了河马,异想天开转弯抹角地说了许多好话,希望河马不再追诉。为了说明儿子并非十恶不赦,也为解脱他自身的世俗压力,他居然对河马说了金琬并非姓何的真实情况。
不过透露之前,他曾再三要求河马保密,并说了金琬母亲有心脏病的风险性。河马当即拍胸保证,指天发誓,说他若不信守诺言,子孙全都男盗女娼,下三代讨不到好死。
然而,楚天这位可怜的老人,护子心切,竟然忘了河马是个流氓无赖。事实上,河马并不在乎他子孙的下场如何,他思考盘算了一夜,第二天便将这桩新情况,一五一十地向白麻子作了汇报。
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待。这时的白麻子,早已是邹司令手下干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尽管邹司令并不怎么把她当人看,但造*有理,革命无罪是时下总精神。司令自然也不能过分地把她不当东西。加之白麻子本质具备,十分努力,于是委任她分管何家沟一带的革命工作,成了一方红人。
因此,河马向白麻子汇报这类情况,理所当然,于公于私都有必要。
河马家中,白麻子拿文作武正认真听着汇报。她麻脸严肃,神情捏拿得十分深沉。当她听到金琬母亲竟有那么一段风流韵事,而且居然瞒过了她,瞒到了今天,不由升起一股无名的嫉妒和不满。同时也高兴。她暗自思考着,应该怎么去做金琬母亲的这篇文章。不过此刻她没有流于言表。现在是造**当权的时候,作为一方的头目,讲话听汇报,自然要注意点身分和派头。
听罢河马汇报,白麻子拔下口中香烟,弹弹烟灰,嘴一撇,大加赞赏河马高度的革命觉悟。表扬他反映的情况及时、重要。最后,她问河马:
“你对这件事有啥看法呢?”
河马大智若愚:“我正向你领教咧。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白麻子哼了一声:“当然是真的。这事我早就看出来了,那死女子的长像、脾气,全都不像我们那一蔸人。原来倒底是个野种!”
“我看也是。你们哪一蔸人,就她一个人长的特殊。”河马附和。“再说,周边方圆都晓得,何楚天是个不说假话的人;他把那件事说得明明白白,头年八月结婚,过年就生娃子。我晓得,人口册上有登记,那女子的确也是二月初二出生的。还有,头年八月结婚,你大哥大嫂也去了。”
“何贤海死了。”
“你大嫂还在呀,她能证明。”
“要球个啥证明?我敢断定她就是野种!就是老覃偷人生出的野东西!哼,你看我咋整那对老少不要脸的女人!”白麻子狠狠地一咬牙。
“这样儿说,你就是证明?”
“啥意思?”
河马阴阴一笑:“我今天除给你汇报,还想请你帮忙咧。”
“帮啥忙?”白麻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