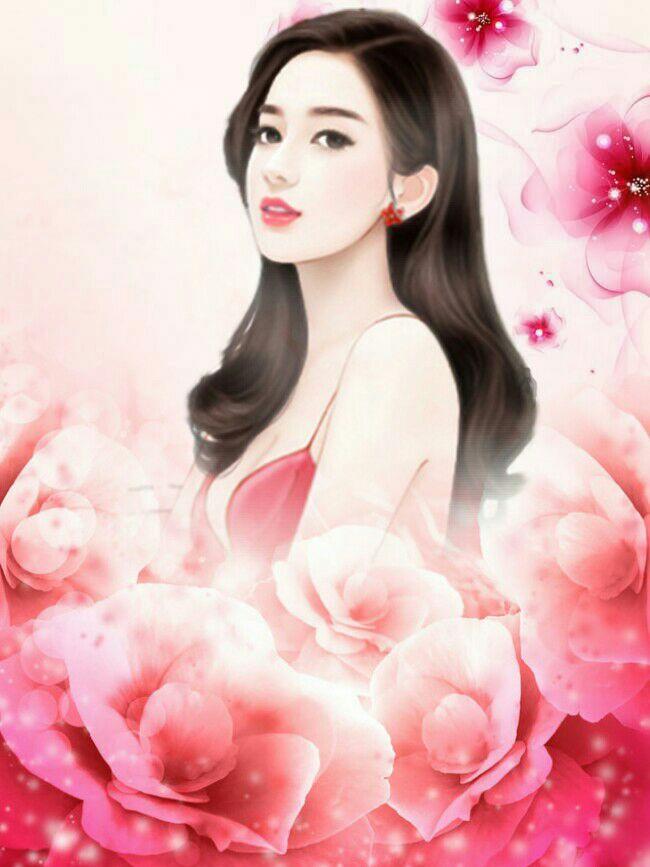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太子妃今天也想死(穿书) > 第204章(第1页)
第204章(第1页)
歌声停了,殷明垠抱她躺到花丛,温存柔软的吻落在她的眉心,然后是眼皮、鼻尖,最后印上唇瓣。
顾西瑗眼还未抬,手已经摸上去,勾住殷明垠细腻如雪的腰肢,将他拉下来,压进黄灿灿的花丛里。
她不再像从前一样粗暴地摔他,却会调情一般稍稍施力,看他乱了额发,蓦然被她压住微微喘气,瓷白的脸颊很快爬上微红,凝视她的黑眸却足够沉静,缱绻情深。
顾西瑗捞起少年的腰肢,埋下身深深吻他,指尖拂过民族布袍上的流苏和银饰,沿着脊骨攀爬。
她衔住花蕾般的唇,指尖深陷入腰窝,看见殷明垠眼尾的泪痣由黑转红,凝成一颗朱砂,情香一丝一缕,抽丝剥茧,从他的肌肤溢出,每一缕香气都是盛放的爱意。
他唇中藕断丝连的轻吟在她的亲吻下碎开,手腕被擒住压进花丛,腰肢又薄又软,垂下流苏与银饰。
山风吹开馥郁的情香,四周灿烂的向阳花在阳光下起舞,整片花海就像被一颗火种点燃,花香四起,绮丽迷幻,蝴蝶从四面八方飞来,围绕着花海飞舞、起落。
他们在花海里肆意拥吻,在盘绕的蝴蝶下诉说情话,顾西瑗伏到殷明垠的胸膛,凝望少年湿漉漉的眉眼,他几乎裸身躺在花丛,湿润的薄汗黏腻了额前碎发,被她轻轻梳理开,印上一个怜惜的吻。
二人缠绵过后,会去山溪里洗澡,殷明垠免不了又在那挨一顿欺负。
清凉的涧水飞泻,光滑的溪石在太阳下发光,少年长发湿漉,一身银饰璀璨交辉,紫衣下摆流入溪水中,这般坐在溪石上,像山中的精灵,水中的鲛人。
顾西瑗与他相拥亲吻,揉着腰,将他拉下水,二人辗转在浅水滩涂,山涧流下的清溪漂着花瓣,沾上少年如云流散的墨发,美轮美奂不似人间。
累了相拥躺在溪边,衣裳很薄,太阳很快就会晒干。殷明垠阖眼休憩,身上软得松了骨头,很快沉入梦境。顾西瑗把他抱到树下清凉的阴翳里,吻了吻安睡的眉眼,起身去山上翻翻找找,寻来一种叫“甘枝”的草叶。
这是这片山里独有的草,芪月人拿它和另一种普通草叶混合,吃下有避孕的作用。
顾西瑗将两种叶子捣烂成汁,喂殷明垠喝下,她自己拾掇拾掇把碎叶子嚼了,这才安心舒坦地躺到他身边,搂着人一起入梦。
这般自在舒坦的日子过了三个月,一行人恋恋不舍地重新启程,离开芪月族前往北疆。
临别时,几乎全村都来了,浩浩荡荡的村民们一路送到村口,光是村民赠送的礼物就装了一车,刘村长拉着殷明垠的手,涕泪直流,道是芪月村始终是他与妻儿的家,房屋会为他们留着,随时都能回来。
殷明垠换回了中原汉族的长袍,玉冠束发,翩跹流入腰下,当众与村民承诺,从今往后,芪月人再也不是黑市上明码标价的物品,朝廷会予流落在外的芪月人庇护,严厉打击捕猎与贩卖人口。
车轮碾过山路,弘遂骑上高头大马,与追在后面的小童们挥手道别,马车驶出很远,顾西瑗揭起车帘,还能看见村民们在村口挥手。
“像做了一场梦。”她放下帘幔,怅然若失。
那场梦里,她和他都只是最普通的芪月族人。
他们在铺满花朵和纱幔的小屋里成婚生子,在开满向阳花的山坡上唱情歌,在星空下的篝火边牵手跳舞,无忧无虑,无欲无求,耕种织造、儿女绕膝地度过一生。
殷明垠把她揽到怀里,抱在膝上,吻了吻眉眼:“我们还能回来。”
“真的?”顾西瑗靠到他肩上。
“嗯。等战事完毕,朝廷沉疴肃清,孩子们长大了,能独当一面,你我便携手归来,在此白头偕老。”
顾西瑗好像看见一对白头发的老爷爷老奶奶在篝火边跳舞,在向阳花开遍的山坡上唱歌,不由啼笑皆非,摸了摸他的下颌:“你跟我画饼呢,那得多少年后了。”
“只要你想,孤随时陪你回来。”
顾西瑗满意地拿脑袋蹭蹭他的下巴,抬手环住殷明垠的脖子,轻t叹一声:“罢了,知道你忙。有机会再说吧。”
一行人继续向北,气候渐寒,半月路途后,抵达了边关禺城。
这座边塞之城乃大夏最后一道防线,石铸的城门高大威严,百姓往来,正值打仗时期,边关将领逐一盘查、严守城门。
进了城,入目全然是北方的建筑风格,城中炊烟袅袅,可见贩夫走卒,处处皆是美食。
弘遂一拉缰绳,兴奋地驱马至车窗前,与顾西瑗说道路边惊鸿一瞥的羊肉泡馍。
不知何时起,她俩成了心领神会的吃货搭子,一路都在寻找好吃的。殷明垠对大部分饮食兴致不高,只偶尔陪顾西瑗尝一口,也不太喜欢的样子,便只剩他俩叨咕了。
“这算啥,等落脚了,我带你见识见识别的。”顾西瑗一瞧这傻孩子的兴奋劲,就知他是第一次到北方,看啥都稀奇。
她放下车帘,隔绝冷风,回身理了理殷明垠身上盖着的玄色裘绒,依偎着他,抵额探了探温度。
他近来受了风寒,恹恹的不爱动弹,连飞醋都不吃了,今晨在车上发了一阵低烧,好在没烧太厉害,用冷帕敷了一会儿就降了温,状态却还是不好。
好在入了城,待会儿去城里药铺取些药,吃了应是就不难受了。
“明垠……”她软声哄他,将裹着裘绒暖融融的少年抱在怀里,抚摸他柔如黑缎的长发,吻了吻鬓角,“没事,我在呢,咱们进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