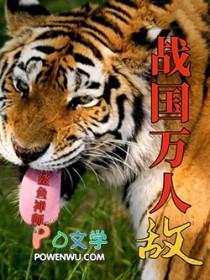葫芦小说>九皇叔 > 第182章 阿雨你别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第4页)
第182章 阿雨你别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第4页)
她一把抓起他的手,就这手背狠狠的咬下去。
一人一口,才算公平。
他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任凭她狠狠咬着不撒口。鲜血源源不断的往下淌,滴落在床褥上,一点一滴的渗透。他看着她那发狠的模样,勾唇笑得邪魅无双。
终于,她松了口,满嘴的血渍,就像此人的魔。
迎上他双眼的那一瞬,她却红了眼眸,“不疼吗?”
他低眉望着自己的手背,鲜血淋漓,一眼看上去,何其触目惊心。
“还生气吗?”他问。
夏雨摇头,又急又气的爬下床,取了纱布和金疮药回来,蹲在他跟前为他清理伤口。赵朔的视线一直随着她,来来去去的,而后温柔的望着蹲跪在身前,红着眼睛抽着鼻子,为他处理伤口的夏雨。
她是难过的,也是舍不得的。可不咬上一口,怎么能让她心疼呢?女人的心,疼着疼着就刻上了他的专属,再也放不下任何人。
伤口很深,一排清晰的齿痕,就这么。裸。露在他的手上。指尖轻柔的抚过还在流血的伤,她抬头,险些掉下泪来,“你是傻子吗?我咬你,你也不知道疼?若是疼,怎么也不喊出声来?”
“男人喊疼,不是很矫情吗?”他低头吻上她光洁的额头,“何况是你咬的,多疼都得忍着。”
她忍着泪,为他缠上厚厚的纱布,“这两日不要碰水,也别再让伤口裂开,还有——如果有红肿或者不舒服,就去找辛复。”
赵朔嗤笑,“哪来如此脆弱,不过是皮外伤。每日,你替我换包就是。”
夏雨点了头,徐徐站起身来。
他握住她冰凉的手,在自己的掌心里捂着,“失望或者希望的时候,我在;难过或是开心的时候,我也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天塌了,爷给你撑着。累了,爷借个肩膀给你靠着。只是有一样,你必须记住,做我赵朔的女人,首当其冲不许妇人之仁。”
“所谓的妇人之仁,除非是有骨肉血亲之人,其余的人与你没有半点关系。人活在这世上,何曾欠过任何人,那些说什么欠的,只是无力抗争的托词。为不值得的人,做不开心的事,没必要。”
她坐在他怀里,抬头望着桌案上跳跃的烛火。心,微微疼着,双手不自觉的环住了他的脖颈,低哑的呢喃着,“我以后,再也不咬你了。”
“本王的猫儿不准备留爪子了?”他嗤笑。
“赵老九,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你就跟爹一样的照顾我。真的,有爹的感觉。”她靠在他怀里。
说这话,赵朔可不愿意了。
爹?
那是个什么辈分?
他哪里像她爹了?
他转身将她置于床榻之上,蹙眉端详着身下的女子,“爷如此风华,怎么可能有你这么丑的女儿?”
她撇撇嘴,“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哦!”他装傻充愣,“那便叫一声听听。”
她一记老拳捶在他胸口,“赵老九!”
余下的话,悉数被他的吻吞没,温柔缠绵,连骨头都酥了。舌尖扫过她的耳垂,带着蚀骨的温软,“爷受伤了,这次真的要你来。”
她一怔,却是笑得眸若弯月,“好!”
翻身,将他反压在下。
对于任何人,赵朔总是一言九鼎,可对于夏雨,他觉得自己一直在打脸。说好了不去镇远侯府,可到底还是不放心她,亲自带着她上门。
有时候想想,跟女人讲什么道理呢?
明知道她不讲道理,你还要讲道理,不是自寻烦恼吗?
何况,这个女人还是个流氓地痞。
谢环正在书房里,拟定镇远侯府的规矩,自己远嫁大夏之后,她是真的不希望镇远侯府就这样没落。谢蕴是谢家唯一的血脉,她所希望的只是这个唯一的谢家男丁,能撑起整个谢家,撑起十数万的谢家军。不管自己在或者不在,都能独当一面。
青云泡上一杯茶,“郡主,歇会吧!”
“新夫人还没进门,这疏影一人独宠,绝然不是什么好事。”青玉轻叹,“小侯爷日日都去流澜阁,如今整个镇远侯府的人都知道,疏影的话比谁的都好用,怕是将来也不会有人将新夫人放在眼里的。”
“小侯爷自有分寸,想来也不会太过厚此薄彼。”青云将茶盏置于案上,“郡主的字写得真好看。”
谢环长长吐出一口气,“议和之约即将敲定,想来我在这京城在自己的国土上,也待不了太久。蕴儿恨我也好,原谅也罢,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青玉点了头,“郡主放心,小侯爷刚刚出去,约莫要傍晚时分才会回来。在他回来之前,流澜阁那边一定已经处理妥当。”
闻言,青云垂眸,“只怕小侯爷刚处于甜蜜之时,心里头势必会有些怨怼。到底是少男少女,一腔心思都在你侬我侬之中,难舍难分的。”
“过段时间,就没事了。”青玉道,“不就是个女子吗?天下漂亮的女人多的是,镇远侯府又不是没有女人。要多少,咱就给侯爷找多少。花里胡哨的都可以,就算要青楼女子,也不能要疏影。疏影来自睿王府,将来郡主远嫁大夏,一旦疏影与睿王爷有所交接,这镇远侯府就会变成睿王府的附属。”
青云瞧了谢环一眼,轻轻点头,“话是这么说,只不过——”
还不待她说完,管家在外头叩门,“郡主,睿王爷到,此刻就在花厅。”
听得郡主应承了大夏的婚事,这两日上门送礼的也不在少数。睿王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偏偏是今日。
“还有谁?”谢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