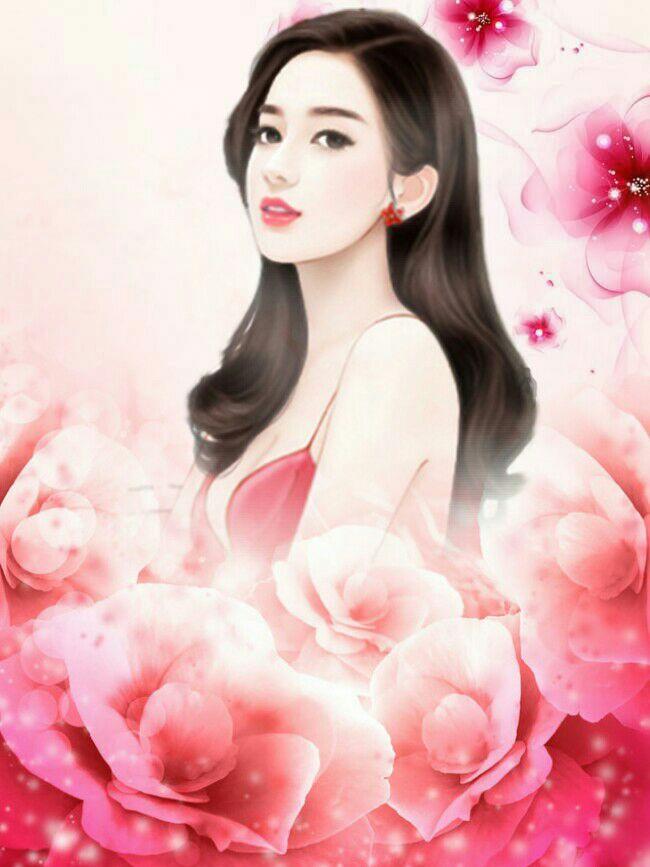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歧途:我一生的岔路 > 第一百三十五章 异乡团聚(第1页)
第一百三十五章 异乡团聚(第1页)
几乎是砸锅卖铁,好容易凑足了五十元。
五十元寄走的第二天,又突然收到黎明来信。信中只字未提他饿肚子的事情,只说他在学校近况很好,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也不错。他说自己的确像林黛玉进贾府那样去做的,不曾出过任何小事。除此,信中侧重说了毕业分配艰难的事。大意是,学校对中专生的分配已经爱莫能助。即将毕业的学生们人心惶惶,全在各托门路,自作努力。这更让卯生的心无限沉重。黎明信中最后说到:入学时,补考了去年休学未考的十一门课程,每科补考费五元,学校催交。
完了,好艰难寄走的五十元,儿子一分钱不落尚差五元。从此,卯生日日奔走,终于一天那位朋友的爱人出院了,并很快办理了贷款手续。只是各有苦衷,卯生借贷到手的只有一仟元。幸好又一朋友相遇说起,当时掏尽身上所有,好赖凑够了二百元,并答应再想办法凑个八百或一仟元。
可是卯生等不及了。他心已经飞向石岩,说什么也要立刻去见儿子,去解救黎明的困苦。人要走,家中妻儿还要做些安排。于是他买了些煤炭之类必须品,又为妻子留下七十元安排庄稼。两百元花尽了。农历三月二十六清晨,他怀揣一仟元登车赴石岩。
这时的石岩,早已是省辖地级市了,一个新兴繁华的移民城市。
石岩街头,似在意料之中,实为意料之外地见到了黎明。父子相见,分外惊喜。相互快步迎上去,卯生老远伸手按住了儿子的肩膀。黎明轻轻侧身,接过父亲另一手上的提包。父子相互注视着对方的脸,居然默默无言,许久没有说话,内心像是阔别了很久很久,相互心中仿佛都有说不尽问不完的话,却又被一团酸苦的东西堵住了喉咙,令人吐不出来。
很久后,卯生朝旁边指指,父子俩便朝街旁房前台阶走来。这里稍显僻静一些,在黎明相扶下,卯生疲倦地坐在台阶上,再次仔细端详站在面前的儿子。黎明身着绛红色衬衣,衬衣扎在蓝色长裤之内,脚登干净的黑色皮鞋,一身整洁,显得文秀、洒脱。猛看,绝对不像穷得吃上顿沒下顿的人。但卯生此刻盯的是儿子这张又黑又瘦的脸。心酸中,他忽然想起仲甫信中对哥哥描述的那句话——“黑得极不健康,瘦得眼眶内陷”。仲甫信中写的是黎明生产豆芽时的形象,而今这句话,不仅是此时此刻黎明形象的真实写照,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卯生的心在抽痛。
他稍歇一口气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马上给儿子买吃的。
“等一会儿吧,等会儿,仲甫可能会来的。”黎明说。
“你说什么,仲甫?”卯生突感惊喜,又仿佛不相信自己耳朵似地追问:“你说仲甫?他能出来?”
黎明抿嘴一笑,带有苦味地说:“他在里面表现很好。有时请假,有时是出来买菜,能够经常独自出来。昨天我们见面,约好今天来等您。”
“噢。”卯生似有一丝莫名的欣慰。想想,他又问黎明:“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这里?”
“凭感觉。”黎明浅浅一笑。然后带有忧伤,又有几分不好意思地说:“不晓得咋回事,我这阵总感到好想好想您。还总想着,您正月回去时车上饿肚子的情景……因为想您,这几天,我经常想去车站等您。再说,您正月不是说过要来石岩吗?我想您如果来,就不会超过这个月底。”
卯生拉起儿子的手,两个大拇指在儿子瘦骨鳞鳞的手背上抚摩着。他想起“人体是感应器”一说。父子之间血缘相通,心灵感应自然特殊。但更为实际的,他想儿子是因饥饿才这么渴望父亲的到来,也相信父亲会来,才有这种所谓的“感应”。
这种渴盼亲人的滋味,这种信赖的程度,恐怕衣食无缺人是无法感受的。
父子俩到了又一个地方,并排坐在闹市边的街沿上,一边等仲甫,一边谈论着父子分别之后的相互间的各类情况。约一小时左右,仲甫果然来了。
仲甫来时,黎明远远就看到了。顺着他指的方向,卯生也很快在人丛中辩认出了仲甫。这刹那间,他竟感到周身汗毛炸了起来,那种渴念已久的,久别重逢的欣喜是那么热烈,那么激动,令他起身相迎时,大脑一阵晕眩,居然有种梦境般的感觉。仲甫身着白衬衣黑裤子,远远看去倒也高高大大。他头戴一顶宽沿草帽,看去似带几分“破帽遮颜”的味道,但他步伐有力,目不斜视,十分洒脱而渴切地直奔卯生走来。卯生抑制着晕眩,不禁趋前两步,细细端详着儿子。这是一年多以来父子俩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兰山的一个建筑工地上,那是在人监视下的匆匆一面。
儿子竟然明显地长高、长壮了许多。只是原国字形的脸瘦了一圈,显长了一些。但那脸上,原有的带几分娃娃般可爱的稚气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过去没有过的成熟和深沉,有了些可喜的成人风采。是呀,儿子已经十八岁多了,成人了。
是的,任何灾难和打击,都只能加速却无法遏止人的成熟。这恐怕也算灾难中的收获。
父子俩百感交集地相互凝视中,卯生有千言万语想说、想问,也想歉意地对儿子道声“对不起”;更有一肚子的恨铁不成钢的怨愤想发泄。可是他嘴唇几度颤抖,几度翕动,最终迸出的竟然是:
“走,我们去下馆子。”
一家条形深邃的小餐馆中,父子三人团团围着一张圆桌,叫了三碗肉丝面。由于热和渴,卯生又狠心叫了一瓶啤酒。囊中羞涩,卯生不敢过分花钱。不过“肚饥糠也甜”,对一双可怜的儿子而言,有此恐怕也算心满意足了。只是他心有种愧疚绞痛的感觉。他握着开了盖的啤酒瓶子,定定地望着一双难得一聚的儿子。
这瞬间,他思想竟是那般不受禁锢、不受约束地飞驰到了孩子们的童年;仿仿佛佛中,他看到的是一双手牵手的娇儿,看到了一双孩子正于踉跄学步中朝他奔来,正向他招手,正呼叫——不,孩子们忽然间又捧起了碗,正吃饭哩……他惊疑中下意识地摇摇头,一擦湿润的泪眼,终于回到了现实。现实中,一双儿子果真正吃饭,而且吃得都很香。他油然着一种酸酸的,一种母亲才能享有的幸福感。是呵,自孩子们出世以来,他的内心深处,确实兼有母亲般的痛爱与情愫。只是无限惭愧,事实证明他这位“母亲”做的很不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