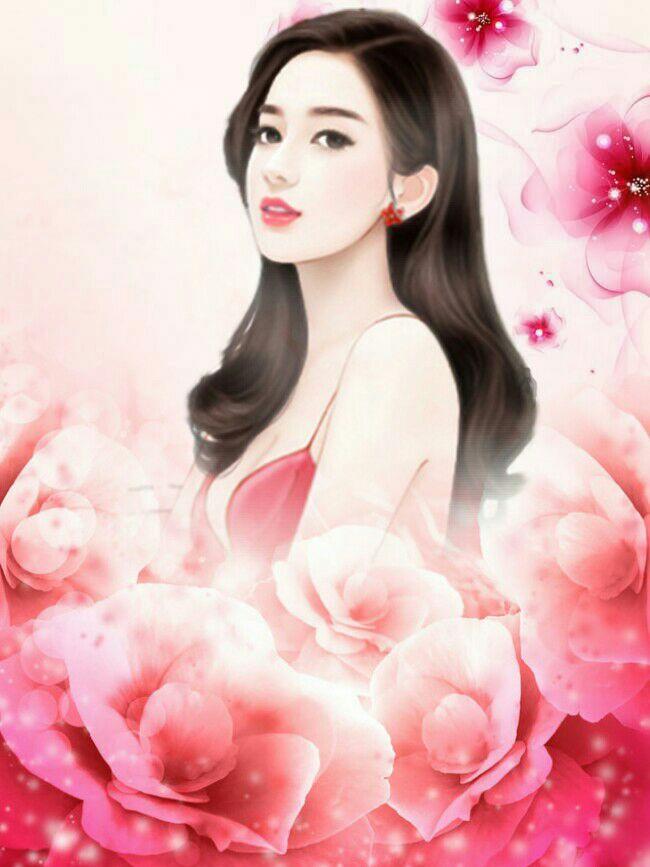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歧途:我一生的岔路 > 第三十五章 云开雾散(第1页)
第三十五章 云开雾散(第1页)
金琬并没有像卯生那么紧张。她拉伸衣服,似嗔非嗔,含羞带笑,火辣辣地看了卯生一眼,索性转身来走到书桌边坐下,说:
“还该我感谢你咧。要不,掉下去就是残疾。”
金琬显得洒脱,大度。她后一句话颇具诙谐,令卯生顿消紧张且噗嗤一笑。待心跳渐感平静后,他下意识偷偷看一眼金琬胸前,幸好那东西还是那么高,还是那么肉乎乎的,看似并未搂坏。他心想:真不是地方,要不,就该去帮她检查一下了。
卯生再次递上钱,诚心诚意,说这钱必须还。即使如此,他这辈子也忘不了金琬的好处。因为倘若没有她那十多元钱,他卯生今生就再无机会以自己名义为母亲做套衣服了。那将是一件抱恨永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卯生说的情真意切,金琬无奈,只好接过钱。卯生终于像了却一桩莫大心愿似地舒了一口长气。他依旧坐回床沿上,笑了笑说:
“闹了半天,这下该言归正传,说一说你回来的原因吧,嗯?”
“说来话长。”
金琬轻轻理了一下额发,又随手拉过身后一条长长的发辫玩弄着,平和的脸上慢慢爬上了一丝她惯有的幽怨式的宁静,语气却带几分轻描淡写地说开了她自己的往事,她说她是为解除了一桩荒唐的婚约,而失去“监护”人之后,才被生产队叫回来做活路的——
易文武牛高马大,绰号黑狗熊,又叫河马。其人形象不仅十分邋遢,而且看上去还呆不拉叽,没有生气。但他肚子里装了几滴墨水,为人很鬼,骨子里又赖又痞。国民党抓兵拉夫的年代,正经人家的轻壮年汉子东奔西逃,无不害怕;他却不怕。他当过兵,愿当兵,敢当兵,于是他“卖兵”。所谓卖兵,就是有钱无势的人家,该当兵又不愿当兵者,就出钱买人去当兵;有买就有卖,卖兵者多是胆大的地痞闲汉。如此如此,河马曾先后八次当兵,居然次次皮毛不伤,得胜还朝。他把“卖兵”当成生意,一边向买主漫天要价,一边在军队里趁乱既劫又掳,倒也次次发财,次次凯旋,福大命大。
早在金琬出生前两个月时,在次杯盘狼藉的残席上,河马与金琬父亲开了个玩笑道:听说你的女人怀上了娃娃,我那婆娘也怀了娃娃,凑巧哩;我看这么着,要是你女人生个姑娘,就给我家做儿媳妇。金琬父亲本是忠厚人,但凭烈酒壮胆也不示弱道,如果你婆娘生个女儿,也给我家做儿媳妇?
“好,好,君子一言!”
一对酒汉击掌为誓。如此这般,玩笑虽玩笑,这在当时当地叫做指腹为婚。
不久,金琬出生了,而河马婆娘却生了个男孩。
然而玩笑毕竟是玩笑,而且是酒后。以致双方当事人,早把那指腹为婚事,当作醉酒污物吐得一干二净。年深月久,谁也未曾提起过。
金琬七岁时,其父病故。十四岁时,河马婆娘突然提着彩礼,说是来认亲。并咒骂河马那厮是个该杀的蠢货,是他喝酒灌泡,竟将这么标致的个儿媳妇给忘掉了;幸亏当年同席喝酒的人提起,要不然,到死也想不起来,活活亏死了一门好亲事。
兰山这方人常说:“养儿请人做媒,养女盼人做媒”。河马家提起陈年旧事,金琬母亲虽莫名其妙,却并不十分反感。唯有金琬坚决不同意。对门不远,相互熟悉,一提起河马的儿子,她便想到那两筒白龙似的鼻涕,就无限恶心。可是河马婆娘找来了当年“指腹为婚”时的“证人”,强行丢下了彩礼。此后,河马又亲自领着他的儿子,连续两个春节拜年,每年在糕点彩礼之余,都有一块做衣服的布料子。这在当时当地,算得是有钱人家的讲究、排场了。
但无论河马家如何殷勤,金琬始终坚持不同意。头一年彩礼,她原封不动退回去过三次。可是每次都被那好心的白麻子提了转来。白麻子男人是老三,金琬父亲是老二。由于这层关系,当时身居母队长要职的白麻子,以其身份和气焰,常对金琬母亲训斥道:
“人家河马老表,是这一方的生产大队会计,大人物咧,别人高攀不上咧,你得罪的起?啊!再说了,人家娃子就是读书差点,但有鼻子有眼睛,哪一点就配不上你那死女子?啊!简直是胡闹。给你那个死女子说,这个家我当了,当定了,我看她能反上天!”
金琬母亲是一个懦弱而又十分顾脸面的人,遇事最怕人说长道短。白麻子每来数落她一次,她便犹同大病一场,一睡几天;两年下来,最终气瘀成结,落下了严重的心口痛病,每痛呼天叫地,九死一生。
金琬痛爱母亲,于无奈中将那荒唐之事一拖三年。如此同时,为躲避河马家的烦扰,金琬小学毕业后便托其表姐介绍,出外当了两年多的保姆。不过,世事总是利弊互存。就因为有了这层糊涂关系,有了河马的权势,金琬当保姆期间,才幸免没有被生产队叫回充作劳动力。
“噢,原来是这样。”卯生插话道,“我还认为生产队忘了你这个人,才落得你多当了一年多的‘自留人’呢。”
金琬苦笑笑,又继续说。
比作“自留人”,金琬受益更大的是在卯生酷爱读书的影响下,两年多来她也读了很多书,学到了学校未曾学到的很多知识。同时知道了婚姻自由,知道“指腹为婚”之类婚约不受法律保护。由此,她用尽两年多中每月伍元工资攒下的钱,一次性退还了河马家的全部彩礼所折合的款项,义正词严地解除了那桩荒唐的所谓婚约。如此同时,在知情人刘秃书记授意下,冯吉子立刻叫回金琬。如此这般才剥夺了她“自留人”的权利。
卯生听后沉吟许久。他没有想到,金琬身上还有这么曲折的一段故事,而且还是这么有见识、有拧劲儿。他抬头钦佩地看着金琬。金琬脸色忧郁,显然还浸沉在不愉快的往事之中。为打破沉闷,卯生忽然站起来,挥手一笑道:
“好了,云开雾散,拨云见日。现在不是一切都好了吗?你大胆勇敢地,砸碎了河马强加的封建枷锁,终于获得了自由之身,我该向你表示祝贺。至于做不做保姆,那有什么呢?当今国家主席,也不是终身职业嘛。至于现在,做活路就做活路吧。当下中国人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如斯如是,加你加我,多乎哉,不多也。”
“酸溜溜的,牙疼。”
金琬终于笑了。她专注地看着卯生,目光温情大方,带有挑逗而又含蓄,以致那眼神,给人一种有分寸的大胆和浓烈的含情脉脉。
卯生的心,莫名其妙中有些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