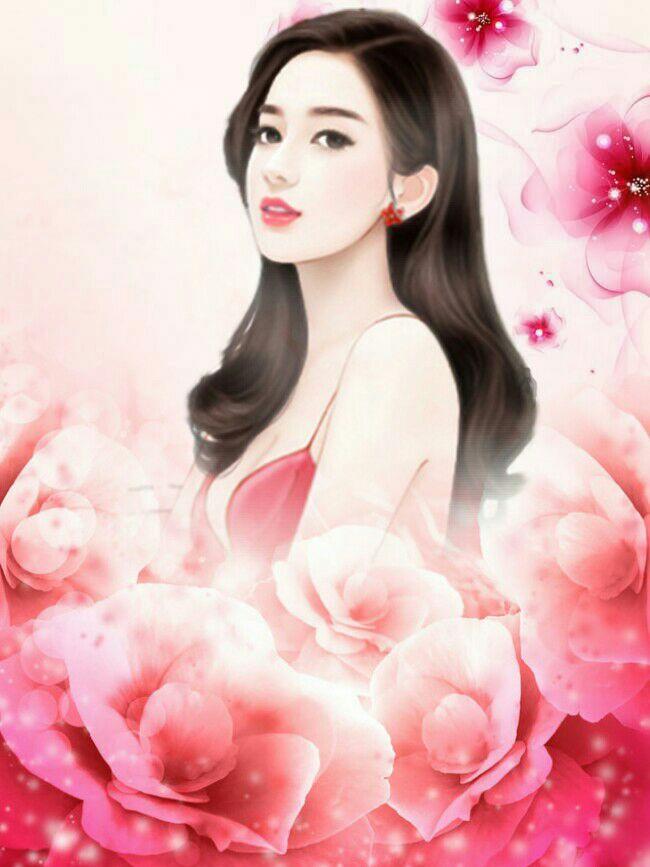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歧途:我一生的岔路 > 第一章(第1页)
第一章(第1页)
这是-部纪实性小说。
这是一卷难忘的记忆。
作家张贤亮说:“人不应该失去记忆,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自己”。既然如此,那就趁尚未失去自己的时候,写吧。以免哪天……失去了自己也就失去了记忆。
人生苦短,短得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眨眼而已。当人六十、七十,悄然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清清晰晰,一切宛然如昨。这大概就是记忆吧?人的记忆中应有美好、有留恋,而本书主人公除此则多了些叹息和伤痛。因为,他看自己身后走过的那条路,走得竟是那么坎坷,那么跌宕,那样的触目惊心,为人也为自己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和遗憾。
人生历程中,风风雨雨,如荡一叶偏舟,前面一派云遮雾罩,仿若处处都是岔路口,何去何从,无人敢不小心,结果却各不尽同:有人凭侥幸、碰机遇,不学无术,瞎打误撞,倒也一帆风顺;不幸者正好多相反,他们或乏权宜,或为人困,或为情困,或自以为是自作聪明,遭遇的则是又一番境遇,别一番人生。
凡人活得都步履匆匆。转瞬到了垂垂老时才得暇回想这许多,似乎也明白了许多,然而逝者如斯,一切都已成为昨天,成为历史。故而这一切中的对与错,一切中的是与非,都无法重来,无法修正。否则,人生应当多些成就,少些过错。不过,语言学家季羡林曾说:“非完美才是人生”。是的,物至而反;老子亦云“物盛则老”;断臂维纳斯者公认更美。故此,不完美的人生或许更丰富,更色彩;也就更值一写,更值供人借鉴。
南北朝人王僧虔也在《戒子书》中说:“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有鉴如此,于是就有了这部书。
写作中,往事如织,喷薄而出,迫人不时扼腕叹息,无法控制地声泪俱下;以致情真语切间人物跃然纸上,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也反映和折射了一段历史的真实。
书的主人公重情人生,敢恨敢爱。他于血、泪、情、仇中摸爬滚打,折腾得轰轰烈烈,生生死死;折腾得可圈可点,可骂可咒,从而留下了这满纸辛酸,一片荒唐。
古语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此言不虚,亦是人类无奈的悲哀。但提起笔来则有不同,白纸待人宽容仁厚,不讥不讽,倒可坦言无忌,任人徜徉,尽情挥洒。人,从生到死,过程而已。延续这一过程的——伟人们留下的是思想、是精神;像老子,像孔子,千年不死。平凡者辈可留的却仅是经历,是故事,也有无从后悔的“教训”。为有益于后代,愿天下人礼待人生而“不吝珠玉”,为自己写出真实、多彩、永久的记忆,以飨后人。
谨以此书抛砖引玉。
第一章童年最是无赖
一九五三年春,卯生刚满五岁。
也许同很多儿童-样,抑或不一样,反正他人生第一最深印象,居然不是天,不是地,而是母亲。
母亲温婉端庄,为人精明善良,待人亲切和蔼;只是她生来体质较弱,给人留有一种娴静的、沉郁样儿的文静感,故其少小时人即送雅号“病西施”。
母亲是位淑女型人物。她与人交往中,脸上总带有一丝很美的让人舒适的微笑。她从不高声说话,从不与人红脸。何家大院里有数十户人家,卯生从没见母亲串过门;倒是院中三妈、四婶之类人物,隔三岔五总来找母亲聊天,诉说一些家长里短,请教些挑花刺绣。她们对母亲很敬重,谈话低声细语,平和斯文。母亲待她们很热情,很随和,相互不时低声说笑,关系很亲近。卯生感到,母亲周围的气氛永远是和畅的。他依偎在母亲身边,总有-种浓浓的幸福感。
讨厌的,与三妈四婶等人谈吐举止相反的,而且每日必来的是一个叫白麻子的女人。
白麻子家住紧邻隔壁,男人也姓何,早年在伪保安团供职时带回了这个女人。据说是用-头毛驴换回的野鸡。有人说那男人做了桩亏本买卖,也有人说其聊算物有所值。白麻子并非姓白,实姓苟,名叫苟步文。人说,对她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白麻子”之称很有由来:首先是她-脸黒麻子坑坑相连,犬牙交错,却又没经没纬的数不胜数。其次是她一张麻脸特黑,黒得妖气、瘆人,令人相见之下顿感厌烦厌恶。也许正因如此,她本人也十分忌讳“黒”字,比如人说天黒了,她宁死只肯说“天晩了”,黒布黑绸类,自然只肯说其是青布青绸了。黒对应白,人们为照顾情绪,投其所好,更重要是熟悉她处亊待人有黒白颠倒的天性和才能,便有意无意间送了她个雅号白麻子。故尔这“白麻子”就叫开了。有时忙中岀错,叫声白麻子她也答应。但旋即是报复:“哼哼,麻子,麻子是天生的,光脸是狗日的。”
对于敢犯众怒者,大家自然不客气,于是“白麻子苟步文,苟步文白麻子”,多年如此重复交替地叫着,口耳相传着。
白麻子三十多岁,干干瘦瘦,人机敏、精神。她脸黑肉少,皮肤绷得挺紧,配上麻坑,迫人不时会联想起那干廋的苦瓜。她的头老向一边歪,给人-种她善于思考的神情与韵味。
卯生很讨厌这女人。据他观察,白麻子每来都习惯性在门外偷听很久。然后才鬼鬼祟祟的,把门轻轻推开五、六寸,同时用几根干廋的黒手指,掐捏着门页边沿,支撑着上身,再将那颗麻脑袋一点一点地送进来;-双贼样小眼溜溜直转,像黄鼠狼寻找小鸡似的搜索-番后,才宛若大虾般地伸直身子,颤颤的,扭捏状地走进来。
苟步文进门第一件亊,便是麻脸热情,语气亲昵地冲卯生的母亲叫声“幺婶”,再逗卯生玩玩,但这一切只匆匆而过,接下便是迫不及待、抓紧时间,自然而又十分自觉地,拿起桌上那只待客用的白铜水烟袋,装烟,燃纸媒。紧接便响起-片咕嘟咕嘟之声。这期间,她手脚麻利,心身配合,吸得很猛,吐得却很慢。吸时,她脑袋微微提动,脖子拉长,好像是为让那股浓烟通过胸腔,经过五脏,直下丹田似的。而吐烟时,她嘴唇则几度颤动,几度强忍,好似万般不舍,一次一小缕地吐着。
每每吞云吐雾后,白麻子即精神倍增。于是便开始重复着她时常爱讲的那些故亊,讲得滔滔不绝,牵丝不断。诸如:东边某家儿媳妇,或西边某某大姑娘——啧啧,不正经。那日,老天大晌午,她亲眼看见那女人与人眉来眼去,令人怀疑。半夜时她去-听,果然,床响。
白麻子天天都能说岀新鲜亊儿。她口齿清楚,善于表达。更难得那麻脸上表情十分丰富,它能随着她的故亊情节,配合岀喜怒羞怯万种情态。特别她那善撇的嘴,一句一撇,竟能撇得人随着她的爱憎而爱憎,随着她轻蔑而轻蔑;直到将假事撇真,真事撇假,红黑撇得你非信不可。
撇,在她嘴上是门艺术。
卯生听不太懂白麻子讲的故事。比如:床响,人家床响有你白麻子啥相干呢?床响,咋就叫人不正经?他想不清楚。但他总喜欢双手捧月般捧着两腮,静静坐着,好奇地看着那张麻脸,动情地看着那张善撇的嘴。不过随着日月迁延,时间一久,他渐次感到那张善撇的嘴撇得很难看了;那麻脸撇起来时抽时搐的,也令人看去有些怪模怪样,惨不忍睹。于是他更讨厌这麻女人,不再巴巴看那张脸。同时他发现,每当白麻子滔滔不绝时,母亲总那么微微含笑地坐着,一句话不说,从不探问,更不附和什么。而且,只要有人走进房间来,在不至于影响大家情绪时,母亲便即刻抽身走开,说去干什么,实际像逃。
白麻子每来至少要抽三次烟,直到那水烟袋铜盒里烟丝被抽干抽尽,才肯怏然而去。白麻子每次走后,母亲都要重新切烟,以备来客之需。水烟袋抽的是烟丝,很细,切起来很费劲。卯生见母亲每次切烟时,都累得额生细汗。他很心痛,却又帮不上忙。由此,他很讨厌白麻子常来抽烟。这天,他想了想,便伏在母亲耳边悄悄说:
“妈,烟装好了,藏着,不给白麻子吃(抽)!”
母亲说:“啥话?来家的都是客。记住,以后不要再叫白麻子,叫苟姐。”
“叫狗姐?不叫。”
“咋就不叫了?”
“吃亏。”
母亲迟疑下,似乎听明白了些什么,她笑道:“傻儿子哟,你真笨!她姓苟,不是狗。你叫她苟姐,是称呼;不是你叫过她苟姐,你就——咳!记住,她姓苟,草句苟,不是你见过的人家喂养的狗……”
“哦,记住了:她姓狗,草句狗,不是人家喂养的狗。”卯生似乎明白地点着头。或许正因此,此后他仍坚持不叫“狗姐”,还是怕吃亏。不过他听母亲的话,从此很少再叫白麻子。迫不得已时,就称“你”,或学人叫“那个麻家伙”。
白麻子依然天天来抽烟,母亲依然天天切烟丝。由此,卯生仇恨白麻子,恨得直咬牙。-天,他总算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而且独自高兴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