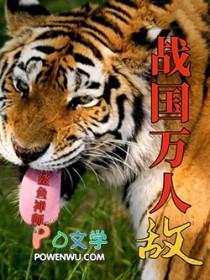葫芦小说>七零边疆二婚妻 > 第449章(第1页)
第449章(第1页)
三蛋抱著小卫星,正准备去哈工傢串门子,跟那放小狗儿似的,放妹妹跟哈工傢的卖力耶两个玩会儿呢。
他说“这你就不懂瞭吧,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不哼,所以你挨的打多,他哭的凶,所以妈顶多也就屁股上抽一下。不信你看著,他马上就出来瞭,你信不信?”
二蛋一直以来,唯独嫌大哥太菜,没发现就挨个打的事儿,裡面还有这么多的玄机。
他站隔壁墙上张望著,果然,就见大哥揉著屁股出来瞭。
一瘸一拐,时不时的还要嗷的哭一声。
“丢人,真丢人,聂卫疆我告诉你,我就是宁肯疼死,我也不会像他一样,动不动就哭。”二蛋说。
而妹妹呢,看看大哥,再看看二哥,坐在三哥的怀裡,大概觉得那个都有理。
不过,她也不知道,狠心的妈妈要出门的时候,准备把她给寄放在哪儿呢。
陈丽娜对于聂卫民开始这件事儿,已经是够惊讶的瞭,结果,等晚上给妹妹洗完澡,把妹妹给哄睡瞭,聂工犹豫良久,就把当时发生在巴音郭楞的事儿给陈丽娜讲瞭一遍。
“你说,聂卫民是故意撞的王小武,还是无心撞的?”聂工把这个疑问,抛给瞭多活过一次的陈丽娜。
他当然不愿意相信儿子是主动撞人的,但万一是呢,那该怎么办。
陈丽娜有没有好的,教他认识错误的办法?
接孩子
陈丽娜听完,沉默瞭很久,问聂工说“万一他要是故意撞的呢?”
“你明白的,恶人,为恶的时候,自有一套说服自己的逻辑,但他那套逻辑,绝对跟现实是相悖的,也是违反法律的。所以,我特别苦恼,我不知道怎么把儿子给教育成这样。”
要聂卫民真是故意撞的人,在聂工看来,真不教育,养大就不是黑社会,而是杀人犯瞭。
“你最近总是饮食难安的,我还当你实验室有事儿呢,你是为瞭这个?”
“是,大黄鱼就丢瞭,也不要紧,但卫民要真的心术不正,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啦,这事儿你就教给我吧,我有办法教育他。”陈丽娜说。
聂工一下来兴趣瞭“真的?”
“真的。”陈丽娜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既然上辈子这是聂工的无解题,那还是不要让他太操心的好。
车到山前必有路,她总会想个办法,一次取瞭聂卫民的毛病的。
这不,马上就准备要走瞭,陈丽娜还得回厂裡安排工作,给自己请假。
“丽娜,咱们厂今年上半年的盈利报告出来瞭。”贺敏拿著计划书,风尘朴朴的就进来瞭“你猜怎么著,净利润五万块,我就问你,你见过这么多的钱吗?”
投産一年,刚开的时候矿区给瞭9万块的备用资金,如今不但还清,还整整赚瞭五万块钱,对于一傢远在边疆的毛纺厂来说,这个业绩确实是够喜人的。
这证明,每一个月,毛纺厂的净利润都将近有一万块。
“我现在想著吧,你那辆车也太旧瞭。你知道吗,现在新産的北京吉普,价格三万一,又新又宽敞,比你那臭烘烘的老吉普强多瞭。怎么样,咱们购一辆吧,我不用,就给你用。”贺敏又说。
陈丽娜就笑瞭“你天天开著老红旗四处逛还不够,又看上我的老吉普瞭?”
“哪能呢,咱们毛纺厂最辛苦的人就是你瞭,你说咱们吧,拿的都是死工资,也变著法子享受一下嘛,你不是爱车嘛,改天咱一起到乌鲁给你提辆新车,怎么样?”
陈丽娜就笑瞭“赶紧忙你的去,钱呀,给我在账上好好儿的放著,你要再动这些歪心思,贺敏,我就把我的老红旗收回去,不信你看著。”
贺敏也是无奈瞭“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陈丽娜,你看著精明,就是个榆木脑袋,你说咱们苦瞭这么久,为啥就不能享受一下。”
“我就是榆木脑袋,而且,我还是那句话,谁要想著买车搞腐化,谁就给我从这毛纺厂裡滚出去。”
胡素是毛纺二厂长和服装厂的主要负责人,听贺敏跟陈丽娜两个吵架呢,也进瞭她的办公室,当然也是想研究一下,上半年的利润该要怎么分配的问题。
突然,有人敲门瞭“陈书记在吗,请问,你们的会计焦来娣在不在岗。”
“在啊,怎么啦?”
“我们是自治区检察院的,她被查证收受贿赂,现在得跟我们走一趟。”两个穿著青色制服,戴著大簷帽的同志给陈丽娜敬礼,并跟她握手。
然后,俩人说明来意,给陈丽娜看瞭逮捕令,就由陈丽娜带著,去找焦来娣瞭。
自打上回焦来娣给组织的人提走,调查完之后,该上班还是上班,该工作还是工作,一直在岗工作的。
隻是,她再也没瞭原来那种活泼,以及,往上爬的劲儿,当然,谁也不理,跟谁也不说话,就隻是做著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
就今天,见贺敏进来报账,她跟贺敏多聊瞭几句。
“我真是没想到,一个大厂要赚钱,居然这么难,咱们厂整整开瞭一年瞭,才赚瞭五万块钱,大傢都兴高采烈的。”焦来娣说。
贺敏说“可不嘛,一批佈才能卖多少钱啊,八百多女工全要发工资,还要给矿区纳税,还债,养一个厂,可不容易。”
但是贪污很容易啊。
每个农场都需要地膜,而杜啓明手裡掌握著地膜的审批权,很多兵团农场的场长,为瞭能率先拿到地膜,抢到时机让种子下地,五十一百,有时候两三百,隻要见瞭焦来娣,就给她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