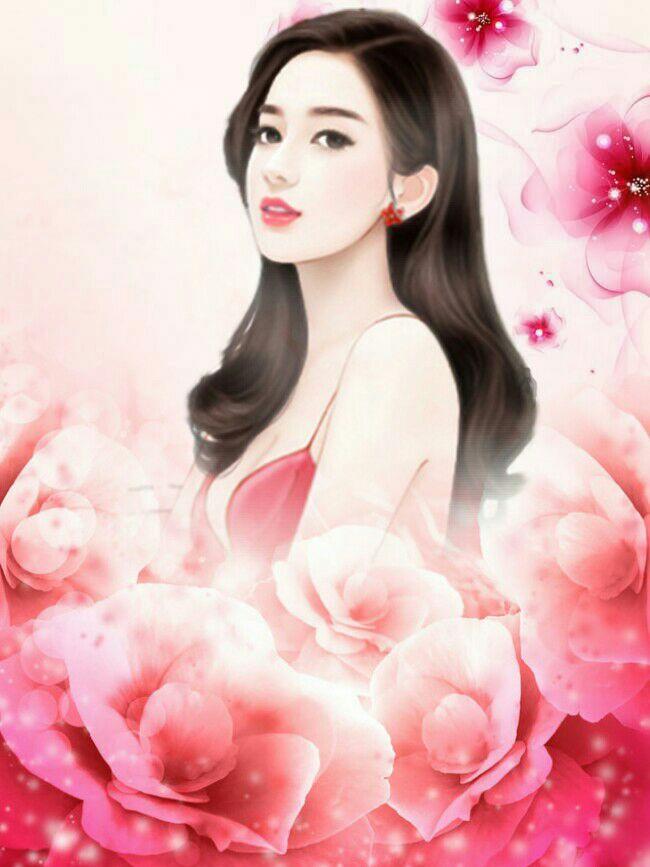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我是村长 > 第237章红色复辟(第2页)
第237章红色复辟(第2页)
李金铸、孙水侯冷漠地看着一个个投票人从自己面前走过,不知道这些上帝在关乎他们命运的时刻做出了何种选择?然而,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当人们经过他们面前
时,他们都不得不礼貌地点点头,致以谢意
计票室里,两台计算机反反复复运转了几个来回,出现的总是那个结果:李、孙二人的得票数相等
“投票的总人数是单数啊,票数怎么会相等呢?”老金拍着脑袋说
“总裁啊,”陈调度提醒他,“有三个人弃权剩余的人数不又是偶数了吗?”
“噢”老金这才明白,单数并不能解决票数相等的问题,“可是,这……这怎么办?”
“请示庾总裁”陈调度建议道
“请示过了他要我们自己拿意见”老金发愁了
“嗯……”看到老金一筹莫展的样,陈调度的脑袋也耷拉下来可是,说来也巧,他低下头,眼珠不经意地往桌上一溜,压在玻璃板下面的《竞标规则》映入了他的眼帘接着,
有一条标了号的附则一下让他开了窍
“参加竞标者,必须首先预缴二百万元押金,方可实施租赁……”
有了陈调度眯着眼睛笑了笑,立刻把嘴附在了老金的耳朵上
“好好,这主意好”老金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返回厂部小会议室,老金开始宣布结果:“同志们,投票的结果很意外经过反复计算,除去三位弃权的人两位竞标者的得票数相等”
“相等?这怎么办?”人们嘁嘁嚓嚓地议论起来
“经过商议,决定这样确定竞标人选”老金一字一句,谨小慎微地宣告说,“根据我们招标的附加条件,竞标人要预缴二百万元的押金因此,我们决定,从现在起,至明天八
点,谁先缴上这二百万押金,谁就优先标”
“‘老八级’,快让大家到银行取款”老金刚刚说完,李金铸就疯了似地喊起来
“大家听到了,赶快去银行取款一会儿人家就关门了”“老八级”也着急地催促大家
“哈……”看到这个场面,孙水侯开心地大笑起来
他看到大家发楞,马上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支票,耀武扬威地对着众人晃了晃,大声说,“这是二百万元,我现在就缴李金铸,你就别麻烦大家为你集资了哈……”
“你”看到孙水侯这样做,李金铸大叫了一声,气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当时,他李金铸就像是倒了霉运,一切一切的事儿都是那么对他不利那个老金,平时见面挺客气的可是,这一竞聘,怎么就向着那个孙水侯说话了呢?是啊,孙水侯有钱,别
说拿出二百万,就是一千万他也照样能拿出来而李金铸和他的竞争团队,都是工薪阶层,必须拿出家里储蓄才行;你老金用这种办法决定租赁人选,不是明显地以钱定输赢吗?
好了老天有眼,多亏自己有这个好儿;洋设备试车让他们老李家露了脸,这一次,矿山机械厂总算是重回到人民手了
他没等组织正式宣布,也来不及与孙水侯办理审计、交接手续,杨总裁与他谈了话,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到工厂,坐到了办公室的皮椅上
“李厂长,这椅孙水侯买的你要换的吗?”厂部秘书看见他的样,提醒他
“换”他一听悄水侯三个字,心生一股厌恶之情,孙水侯,是个什么东西?他不过是个投机倒把的个体户别看在这个厂里当了几年家,他李金铸照样不把他放在眼里
现在,孙水侯按照他的指示,已经准时来到办公室,向他汇报工作了两个人不谈还好,一谈,就是天崩地裂……
孙水侯刚刚谈到如何减人增效的事情,李金铸就冲他大发雷霆:孙水侯,你知道下岗职工的生活是多么惨吗?他们在工厂干了大半辈,你说不用就不用了,你让他们怎么活?
你知道国家培养的那些个老车工、钳工、电工……那些个优秀的技术工人在干什么?他们被生活所逼,有的拉人力车,有的卖苦大力,还有的在靠拣破烂维持生计你为了自己挣钱
,把他们推到苦海里去熬煎,你怎么这么狠心?过去,他们都是你的同志,你的好哥们们儿呀,现在,你这么干,太丧良心了
金铸,不能这么说?孙水侯强忍住心的怒火,分辨说:下岗,也不是咱们一家这么搞,是普遍现象啊过去,工厂里人浮于事,影响工作效率啊现在……
算了,不用说了李金铸听到这儿,一拍桌,说:这种事儿,从今天要纠正过来凡是下岗的原职工,一律回来上班党央要我们关注民生我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金铸,你这么搞,不是要复辟吗?
什么复辟?你那一套才是复辟,你让工人流离失所,那才是资本主义复辟今天,我李金铸回来了,我就是要搞无产阶级复辟,让工人重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
好了好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孙水侯觉得没法再谈下去了苦是别人,他还有办法与他辩论,与他争论个水落石出可是,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亲家呀自己与他闹翻了,将来女儿
的日不好过呀算了算了不就是一家工厂嘛,权当送给他了就他这思想观念,自己想干也干不了哇反正工厂交给人家了,自己干脆就退居二线算了回头,自己与杨总裁、庾省长打个
招呼,自己就坐在家里,当寓公了;至于这厂的事儿,随他李金铸去
离开李金铸,孙水侯坐着车来到了自己的宾馆,觉得格外亲切、温暖这儿是自己的家业,是自己的老窝儿这儿的一砖一瓦都是自己的血汗挣来的那个矿山机械厂,是国家的,
不是个人的现在国家换了别人经营,与自己无关了想着想着,他情不自禁地走进了顶层的办公室他坐下来,沏了一壶茶水,一边喝,一边想……默默地呆到了下午,呆到了天色发
黑的时刻,此时的他觉得分外的愁苦,分外的寂寞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于是就拨了一个电话:英娣,请你到我的屋里来
“别,”英娣见他压上来,连忙说,“孙厂长,别这样”
嘴上这样说,但是她没有拼命地反抗于是她的声音仿佛不是坚决的拒绝,倒像是盛情地鼓励
“英娣,别喊我厂长,现在的厂长是你爸爸了”
窗外头开始刮风,随着阴云密布,丝丝的雪花儿变成了一团团棉花似的白絮飘舞昨天的天气预报本来是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突然从天而降,使这个脏乱差的工业老城一下
显得如此干净如此美丽,一切都像被这洁白的意念净化了从酒店八楼的这个窗口看下去,北辽市像一个纯洁无疵的少女刚刚落成的巴黎西餐厅就在街对面,但是,大雪已经覆盖了
它的红色屋顶一串串黄色的灯光射在雪地上,宁静的马路上仿佛铺上了一床长长的充满暖意的淡黄地毯这才十来点钟,街上几乎没有了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