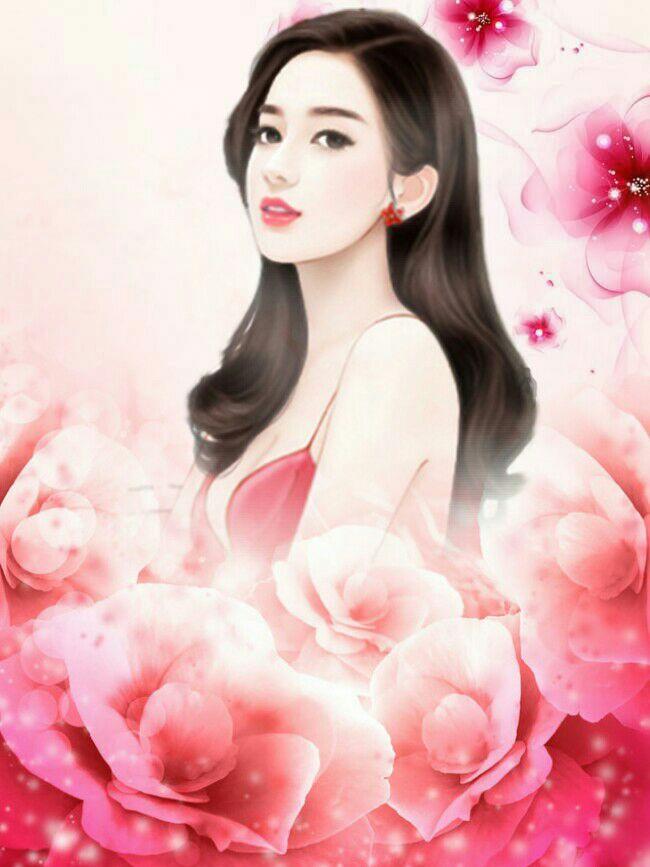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你白月光真棒+番外 > 第37章(第1页)
第37章(第1页)
可惜那个小儿子八岁时被绑架了,至今杳无音信,很多人背地里议论,说这都是傅庭雪的手笔,想吃绝户。
但这些年傅庭雪一直没有再娶,膝下也没有一儿半女,反而坚持寻找失散多年的继子,这倒让人感慨起他的深情来。
傅庭雪抚摸挂在胸前的项链,表情和蔼道:“其实早就得到一些消息了,但他被绑走时年纪太小,什么记忆也没有,他不肯认我,我也害怕吓到他。听说他很喜欢裴导的原著小说,我想哄哄他。”
江恕礼节性地祝福道:“希望您儿子能早点回家。”
至于哄儿子开心这种话,他一个字都不信。
不过江恕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虽然他已经答应裴律的要求,但这样意外得来的利益,他当然也不会拒绝。
临走前,傅庭雪起身握住江恕的双手,感谢对方的退让和助攻。
他的手很凉,像是毒蛇身上的鳞片,那种冰凉的触感让江恕感到很不适。
回到总统套间后,江恕的脸色逐渐冷下来,他对乔西道:“盯着他吧,看他到底想做什么,一旦发现端倪,找到证据,直接举报到上面。”
不作为也是一种错,按兵不动从来不是他的风格。
江恕在二十岁那年正式接过江家的位置,那时候他的爷爷病重,父亲又早早去世,各房的叔叔伯伯都在蠢蠢欲动,都想把他拉下去。
在这种局面下,他出手果断狠辣,直接把大伯全家发配去西伯利亚种土豆,又把不听话的三叔送到监狱里。
有些人本来有机会做狼,他不想做狼,那就得被当做羊吃掉,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妥协和失败。
茶室里,江恕走后,秘书凑到傅庭雪耳边道:“老板,最初的那个狗仔找到了,但他一听到风声就跑了,找人的打手扑了个空。”
傅庭雪点了支烟,语气淡淡道:“那就掘地三尺地找,生死不论,死的最好。我儿子要回家了,我不希望出现有关他的任何不利新闻。”
他的举止依旧优雅得体,但言行中满是冷酷凶狠,这才是他的真面目。
他低头想了一会儿,又道:“让律师团准备一下,他们有活要干了。”
说这话时,他伸手从果盘里挑出一只橘子,慢吞吞地开始剥皮,连白色的筋丝都挑得一干二净。
他的胸前挂着一根照片项链,这条链子看上去并不怎么华贵,也没有镶嵌宝石,因为常年被人握在手心摩挲,反而有些陈旧。
傅庭雪打开合金盖子,露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浅浅地笑着。
巴别塔的236号房间里,屋内黑得就像蜘蛛编织的黑网,桌面上有一只被打翻的酒杯,一个冉冉升起青烟的熏炉。
周济慈使劲掐着自己的手心,强撑着不彻底失去意识,他口中干渴,浑身燥热不安,眼瞳模糊而妖娆,明显是中了催情的药物。
见药效挥发得差不多了,傅伟蹲在周济慈身前,伸手去摸他的脸:“心肝,你看你这又是何苦呢?你要是早从了我,又何必受这罪呢?”
掌下的温凉让傅伟心神一荡,火热的眼神愈发肆无忌惮地扫过他全身,仿佛在他赤裸的酮体就在眼前。
一旁的林琅不耐烦道:“行了,说好的,我先上,你再上,快把他交给我。”
傅伟面露犹豫之色,怎么说呢,他有些后悔答应林琅的要求,他堂堂英贤集团的继承人,怎么都该是他先拿一血吧?
这时,周济慈缓缓睁开眼,因为药物的作用,他的眼眸湿漉漉的,声音颤抖道:“我想先和你做,我还没做过哦……你难道不想要吗?”
他的声音因为药物而显得绵软无力,尾音那点绵软的钩子直听得人心里酥麻。
一旁的林琅气得目眦欲裂:以前在床上都不知道你那么淫浪,果然都是在敷衍我!看着清高得很,原来也是个烧货。
傅伟听得心都酥麻了一半,连忙答应:“心肝,你都这么说了,那我怎么不满足你呢。”
他正要上前扶起周济慈,林琅挡在他身前,不满道:“不是说好的我先上吗?”
傅伟正色欲上头,他脾气暴躁又恶劣,直接一巴掌扇过去,面色狰狞道:“少废话,老子能让你喝口汤已经是大发慈悲了,你也敢和我争?”
林琅捂着脸,气得直咬牙:要不是我偷狗,你他妈能碰到他的衣角都算我赢!
半推半就间,傅伟急色地把周济慈压在身下,疯狂地去嗅他脖颈间的香气,甚至直接上嘴去啃那片百合花一样柔软洁白的皮肤。
因为他的力道,周济慈口中或轻或重地开始吸气,轻chuan道:“傅少,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色欲上头的傅伟头也不抬:“心肝儿,你尽管说,什么事我都答应你,要我的命都行。”
周济慈眼中闪过一道冷光,冷得像是封冻的湖水,但语气却温温柔柔道:“把林琅绑在椅子上看我们做好吗?”
对于这个奇怪的要求,傅伟犹豫:“为什么要绑着他看我们做?”
林琅气得跳脚:“事到如今,你别打歪主意,你跑不掉的。”
周济慈轻柔地笑:“傅少,我没想跑,我只是想报复他一下,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曾经的男朋友和别人睡觉……我和他以前好歹是伴侣,你难道不想这样做吗?”
他说一句就得停顿一下,眉眼间都是隐忍之意,甚至使劲咬着舌尖,拼命让自己保持清醒。
傅伟听得有些意动,怎么说呢,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牛头人的心理。
把老公绑起来,然后当着老公的面强奸他老婆,想想都觉得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