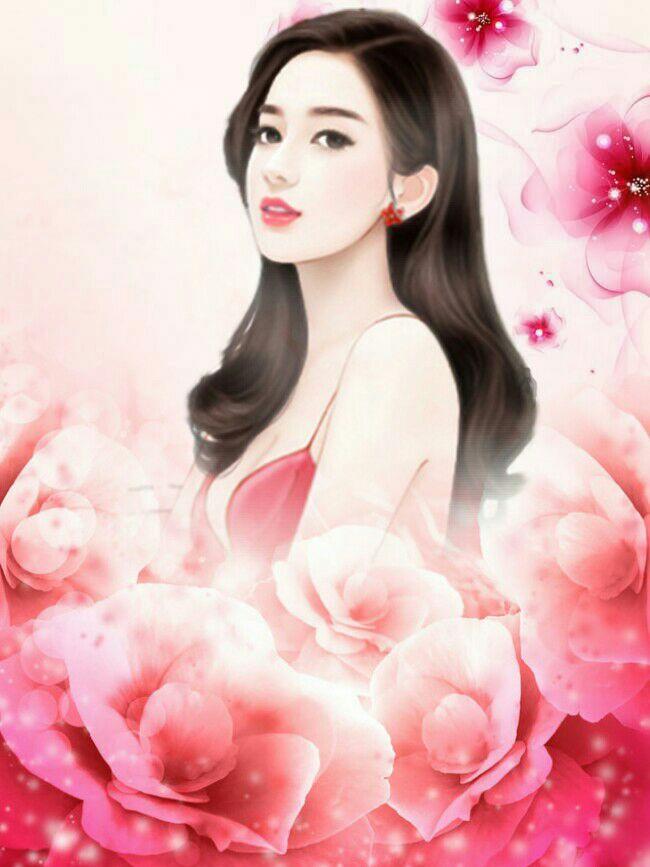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你白月光真棒+番外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他真的害怕江恕发疯对学长做出那种事,学长要是遭受那种事,他想都不敢想。
裴律深吸一口气,语气卑微道:“我没别的要求,总归是我对不起你。我只有两个要求,你要是答应,我立刻就签字。”
江恕讥讽地笑:“事到如今,你还敢跟我提要求?你以为你不签我就拿你没办法?”
怕江恕发火,裴律连忙解释:“不是什么重要的要求,我只求你这两件事,以后我就退出娱乐圈,也离开港城,再也不碍你的眼。”
江恕没说话,他摸着扶手椅上半狮半鹫怪兽的雕饰,表情威严睥睨中透着冷酷。
裴律知道他这是示意自己继续说,缓缓吐出一口气后,他继续道:“第一件事,我会让工作室发出声明,是我先出轨林琅的,所有的道德谴责都由我来承担,而你也得做出澄清。这一切都和学长没有关系,我不想学长被泼上脏水,他是完全无辜的。”
“第二件事,我继续想拍完《金色的传说》,也算圆了我少年时的一个梦……拍完这部电影,我就出国,再也不碍你的眼。”
这两个要求都是和周济慈有关的。
江恕心里冷冷地笑:真是可笑啊,曾经的枕边人在自己面前低头卑微乞求,居然是因为自己威胁伤害了另一个男人。
比可悲更可悲,比可笑更可笑。
不再去想这些荒谬至极的事,江恕让乔西把离婚协议甩在裴律面前,淡淡道:“你的条件我都同意,签吧。”
江恕早就在协议上签好了字,裴律看到离婚协议上的字迹时,心口一痛,鼻子有些发酸。
签好字后,裴律深吸一口气,心里突然变得空落落的。
一切都结束了。
见他签完字,江恕毫不留情地道:“乔西,送客。”
乔西恭敬地做出送客的礼节。
临走前,裴律最后一次回头,轻声道:“对不起。”
对此,江恕只是冷笑一声,他躺在豪华沙发上,一只手夹着雪茄,另一只手磨蹭着自己的金属打火机,打火机冒出滋滋的火花,像是心脏的跳动声。
他仰望着母亲的油画,圣母也不能比她更美丽温柔。
金色的阳光中,他缓缓闭上眼,像是在感受母亲的怀抱。
港城的东郊和西郊之间就隔了条河,一条河的距离,却像一把尺子,硬生生要给人划分出个三六九等来。
和东郊极具现代化的繁华街道相比,西郊的筒子楼显得瑟缩又阴郁,老旧的墙皮层层剥落,被雨水浸染成灰黑色,住在这里的租客们就像这座城市的工蚁,是最辛苦的爬虫。
梨花巷的一间简约狭小的饭馆里,往日热热闹闹的饭馆却显得有些沉寂,倒不是因为用餐的人少了,而是餐客们都若有若无地用眼神瞥向同一张饭桌,甚至连彼此间的寒暄都忘记了。
那张饭桌前有个年轻男人,他点燃一支细细的香烟,慢悠悠地吸着,一张稀世俊美的面容在烟雾后隐隐若现。
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也有些冷淡,在这座热闹喧嚣的小饭馆里,所有人都有些浮躁炎热,唯有他冷冷清清的。
他就像一把缠满玫瑰藤的冰刀,其风采令人一见难忘,却又拒人千里之外,寒冷得能伤人。
和他一比,他对面那位埋头干饭的男人虽然还算得上英俊,但一脸胡子拉碴,加上身上的衬衫皱巴巴的,就显得不怎么惹眼了。
周济慈把手表和耳钉都放在桌子上,说道:“你应该也看到网上的新闻了吧,你拜托我的事估计是不成了。”
对面那男人挥挥手,口齿不清道:“能拍到那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再去托人给你问问,看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能办下来。哦,你放心,草莓我也让人帮你找到。”
男人名叫秦洋,是港城税务局的一名组长,家世也十分不俗。
三年前,他在一艘来自英国的货船上发现了藏在船舱里的周济慈。
周济慈是从英国偷渡来到港城的,他躲在船舱里整整半个月,被秦洋发现时全身都是伤,就差一口气了,秦洋将他送去医院后,他昏迷了整整一个月才醒过来。
好容易醒来后,周济慈对秦洋说,有人非法拘禁他,他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希望国家能为他提供保护,不要把他遣返回英国。
医生为周济慈检查全身后,也确实发现他身体里有违禁药物的痕迹,这些药物会损害人的大脑和记忆,让人昏昏欲睡,整日无精打采。
居然还有人非法拘禁男人,秦洋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荒谬至极的事。
但秦洋看着病床上那张即使苍白消瘦也掩藏不住英俊的脸,他突然觉得这种事好像也变得合理起来。
周济慈那时候身上没有一分钱,连张身份证都没有,秦洋实在心有不忍,帮了他很多。
周济慈这种情况严格来说就是偷渡,但事出有因,秦洋辗转为他奔波,好容易才让他在港城落脚。
但唯一麻烦的就是国籍问题,想要转本国的国籍非常麻烦,一旦周济慈被遣返回英国,后果想都不敢想。
后来,周济慈被林琅带入娱乐圈,也算有了经济来源。
在一个剧组做演员时,周济慈发现剧组的工作人员故意烧掉一间角楼。
他当时留了个心眼,在很远地方偷偷录了像,并把胶卷交给秦洋。
后来这部电影就被爆出重大偷税漏税,就是那场“尼罗河惨案”的全员恶人的偷税事件。
由于这部电影是大制作,为了拍出各种大场面,剧组甚至直接修了一座王城,成本高达数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