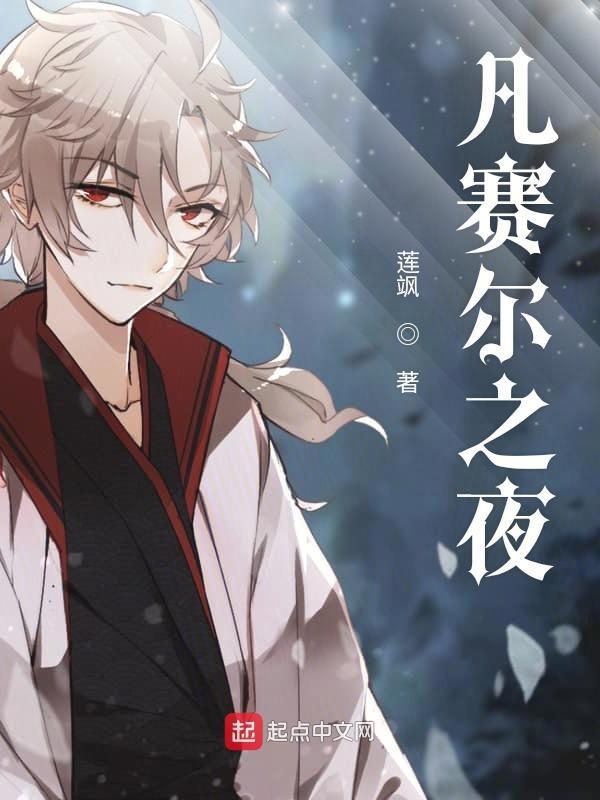葫芦小说>穿越到安史之乱当医生李明夷卢小妹 > 第308章(第1页)
第308章(第1页)
在自己身上实验穿刺技术。
“太危险了。”李明夷脱口而出。
赵良行亦愕然不止。
“有李郎在,便不算危险。”裴之远拢了拢衣领,眼神饱含坚定,“何况将士们为家国出生入死,我等只是以身试针,又算得了什么?”
其余随他而来的医官亦纷纷颔首。
裴之远的目光挨次掠过站在他身后的弟子,最终落在眼前的年轻军医身上。
“现在即便李郎不在,也可以把病人放心交给我们了。”
无数坚毅的视线交汇在眼前,传递出勃勃不息的决心。
李明夷站直了背脊,唯有回以敬意的目光。
“那便有劳诸位。”
将监护室的事务全数交接给裴之远一行后,李明夷便着手开始准备随军的药物。直至天光淡下,他点燃了灯,才发现门口还杵着道高瘦的人影。
青年怀里抱着陌刀,正靠在军医处的门口,神情凝然地想着什么。
“忙完了?”似乎察觉到他的目光,对方懒洋洋打个呵欠,不客气地挑开帐帘,向外使了个眼神。
“走,跟我去喝一壶。”
李明夷挑眉看着他。
无事献殷勤,必有前因。
见他俨然怀疑自己的动机,凌策没好气地瞪他一眼:“我帮你办了事,难道连点报酬都没有?”
李明夷还想再问什么,对方已大步流星地迈进,不由分说将他拉走。
“知道你是大忙人,我请你总行了吧?”
凌策死活将他拉出军营,来到长安城的一家小饭馆。
暮色四合。
晚风和爽地吹过,破旧的幌子在门口招展出一个酒字。门口的台阶下,两个赤脚的老者正盘腿对坐着下棋。店里稀稀落落坐了两三桌,倒是宽敞有余。
“柳娘子,给我们上锅炖大鹅!”青年熟门熟路地拉着李明夷入了座,将陌刀往案上一拍,豪爽地点起菜。
“客官来得不巧,我阿娘去探亲了。”
回话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少年,怕留不住客,一边出来殷勤地倒茶,一边赶紧补了句:“我阿耶手艺也不差,客官们赏脸尝尝?”
来都来了,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凌策回了声好,将茶水挪开,掏出挂在腰上的酒葫芦,咕咚咕咚往空碗里倒去。
“你试试。”他把酒碗推过去,自己则举起葫芦,直接往喉咙里灌去。
李明夷也端起酒碗,仰头一饮而尽。
“不错吧?”青年右腿大剌剌踩在长凳上,手臂搭上膝盖,笑着摇了摇空葫芦。
“不赖。”
凌策还想再说什么,忽然察觉到什么般,耳朵轻轻动了一动。
“你耍诈!”
“我哪里耍诈了?”
“你的棋。”坐在门口左边的布衣老者,指了指对方刚挪动的一枚象棋,“兵卒棋哪有往后走的?”
“凭什么不能?”坐在右侧,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的老者,红了一张脸瞪回去,“我没听过你说的规矩。”
“兵卒当然不可以后退,否则不就成了逃兵?”
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身后的青年,插进的一句话让两个老者同时一愣。
左边的老者反应过来,当即叫好:“这位郎君说的正是。”
右边那位忍不住嘀咕回去:“那这规矩立得不公平,将军尚有败仗而逃的,凭什么士兵只能选择往前?”
青年有趣地勾了勾唇,呵出一口酒气。
“士卒不是因为成为了士卒才往前走,而是决定了只往前走,才成为士卒的。”
“你又不是……”老者还想再争,忽然瞥见桌案上的陌刀,顿时闭上嘴了。
“算啦,就快要收市啦。”左侧的老者收起棋盘,撑着腰杆起身,笑道,“这局不算,明日再战。”
对方便也顺势下了台阶:“好好好,就让你一回。”
两个老者结伴而去,青年仍靠在门槛上,吹着晚风。
李明夷也起身走到门前。
入了秋,天色早早暗下。两旁的摊贩各自拾掇起被挑拣剩的货物,正吆喝着最后一嗓子。
隔壁的酒楼上,客人三三两两结伴而出,趁着宵禁的梆子敲响前回味着方才的滋味。
一种无声的秩序,正重新组建在这个古老的城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