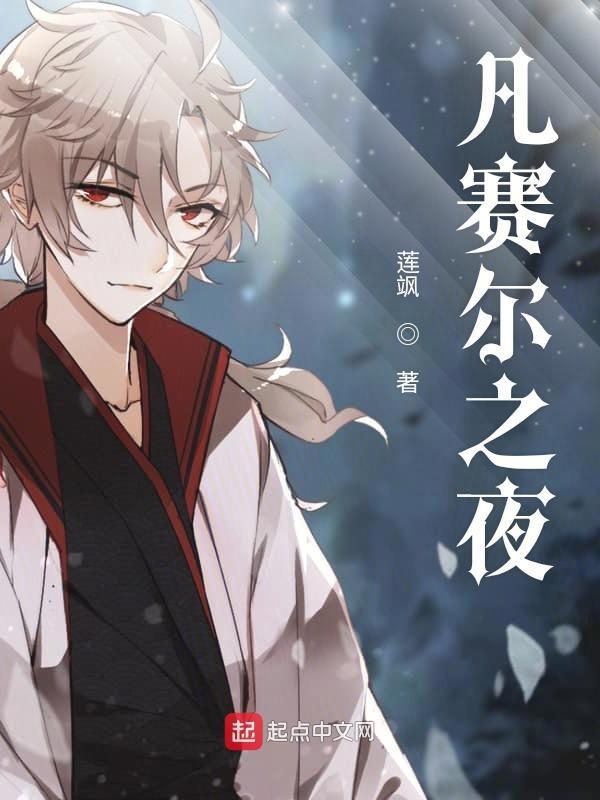葫芦小说>穿越到安史之乱当医生李明夷卢小妹 > 第270章(第1页)
第270章(第1页)
捏在他指头中的草纸已经折出几道深深的痕迹,上头歪歪扭扭写了点什么,又给胡乱涂黑过。那半支笔倒做工精良,可惜只剩半截,看起来写字都很勉强。
李明夷垂眸一看,大概猜出对方的烦恼。
“会写字吗?”
“看不起谁呢?”青年声音蓦地拔高一分,顾忌着其他睡觉的人,马上又压了下来,“我学会好多字了。”
怕对方不信似的,他把那半支笔高高举起,眼睛瞪得大而认真:“这可是将军送我的。将军说了,打仗也得识字。就比如三国时那个吕蒙也不识字,后来读了书才做成将军的。要是想当大将军,就得学写字。”
说到此处,他往上抛了抛笔,视线跟着懒洋洋上下,得意翘起的唇角却耷拉下来。
“可惜这笔折了半截。”那能挂油壶的嘴角咕咕哝哝,“还不是为了护着你们。”
本就半生不熟的字,现在没有趁手的笔,更是见不得人了。
和开罪过的军医们开口提一个借字,又怕遭他们耻笑。
青年烦恼地抓抓脑袋,没好气地瞪过去:“你要敢告诉别人……”
对方却全然无视他的眼神,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半支笔:“怎么不换一支?”
“你说得轻巧。”凌策把笔杆握住,白他一眼。
没钱呐。
毛笔可不是便宜物件,要出军营采买还得向上级通报,要为这么点小事翻出阵仗,他也丢不起这个人。
“只是写一封信的话,未必需要用毛笔。”李明夷端起他面前那罐黑水,举在他眼前,“只要能连续淌出墨水就行了。”
凌策歪着脑袋打量过去,眼神思忖着:“照你这么说,得是中间空着的细管。”
不待对方提醒,他眼睛忽而一亮:“我知道了!”
说着,他便一跃起身,把手里的东西往被子里一掖,风风火火往外头奔去。
凌策这一跑,整个大帐的人都被哐哐的脚步声震醒。眼看着天光逐渐亮起,抱怨也是无用,军医们索性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劳碌。
直到午时,也没等到凌策回来。
他本是郭旰麾下的士卒,平时大剌惯了,周春年也不大管他,只令白班的军医们先稍作休息。
这两天的治疗消耗了大量生理盐水,见水桶见底,李明夷趁空去河边看看。
让他失望的是,渭河的水质实在称得上糟糕。
所谓泾渭分明,其中之一指的便是军营畔这条渭河。眼前还未注入黄河的滔滔大河,泥沙滚滚翻涌,回旋的大浪都带了几分浑浊。尽管没有现代工业的污染,这种水源也绝不是医疗用水的第一选择。
顺着河道往东走了一截,几乎就要脱离军营的范畴,视线中慢慢开始出现零星的房屋。估摸着附近就有可用的水源,李明夷循着马和教学的找水秘方,很快找到一条清澈的溪流。
溪水来源于地下河或山泉,水质明显干净许多。李明夷正打算取一些回去试试,抬头却瞥见一道银色的身影站立在下游的转角处。
看来已经有人比他先一步找到这个洁净的水源。
那人旁边还牵着匹皮毛色亮滑的玄青大马,想是饮马至此。对方似乎也注意到靠拢的脚步声,远远朝他招了招手。
李明夷提着水桶过去。
那招摇的一身银甲,果然是郭小将军。
刚历经一番血战,那锋利逼人的眉眼也挂上几处彩,轮廓更见瘦削。浅浅的伤口添在这张脸上,倒丝毫不减其英气,更显出沙场驰骋的气魄。
这潇洒模样,放在现代,高低也能惹小姑娘尖叫一声。可惜身旁的大马不给面子,长长的马尾烦躁地甩开,鼻孔往天上喷着气,显然正和自己主人不对付。
看清来人的面孔,郭旰当即不客气道:“你来得正好,快帮我看看马。”
说着,便把缰绳往前牵了牵。
这匹马李明夷倒有几分印象,当初九门乡下见过,毛皮黑亮,体格壮硕,一眼便知血统高贵。那线条优雅的脖颈被缰绳牵着,亦无低头的姿态,就连瞥人的眼睛都是高高往下的,很得其主人的心高气傲。
的确是匹骏马。
然而就算不是兽医,也能看出它现在状态有些不对劲。
那身玄青的皮毛仍是油光水滑,却明显松陷了几分;朝他龇出的两排牙龈和嘴皮黏糊粘着,显得有些干燥。
尽管物种大相径庭,哺乳动物都有类似的脱水体征。
李明夷也只是看看:“军中难道没有兽医?”
“兽医说它缺饮水,可我带它跑了三条河,这家伙还是不肯喝一口。”郭旰抬手摸了摸大马的鬃毛,转眸看见那张不为所动的面孔,当即明白对方的意思,忍气吞声地改了口,“还请先生指教一二。”
这话听起来倒顺耳多了。
李明夷也不再和他卖关子:“潼关的岩质和西北不同,将军不妨在水中放些盐来试试。”
“盐水?”郭旰正思忖着这话,耳尖忽然一动,手掌下意识捏紧枪柄。
“你们别追了——!”
下一刻,一道惊慌失措的喊叫便闯进耳中。
李明夷循声看去。
只见消失了半日的凌策正举着大刀从田野中狂奔而来,身后竟还跟了一群扑扑扇翅的白色大鹅。
青年越是窜逃,背后的鹅群越是气势勃勃地乘胜追击,不住往前伸出尖喙狂啄。
“祖宗,鹅祖宗,别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