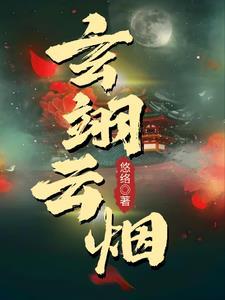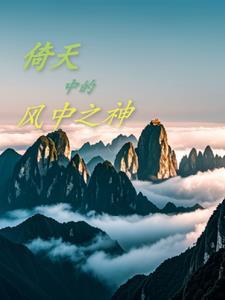葫芦小说>穿越到安史之乱当医生李明夷卢小妹 > 第221章(第1页)
第221章(第1页)
马和在一旁使劲挤眉弄眼——这一听就骗人的鬼话,还能有谁比他更懂骗子吗?
李明夷思忖片刻,还是抽出门栓,将门推开。
扑朔的风卷着落叶一下子涌进,站在风口里的青年燕将金刀立马,身后跟着十数表情肃杀的曳落河士兵。
一见这场面,马和登时脚底一软,暗道一句命不久矣。可对方却压根没看他一眼,表情反倒露出几分欣赏:“听闻我们的勇士在这里兵败数回,郎君果然好胆识。”
这话既是恭维,同时很有威胁的意味。
李明夷自认不擅长口舌之争,也实在没有闲聊的心情,索性直言:“阁下需要什么,但请直说。”
对方这才迟迟地瞟了眼一旁身穿道袍,衣服上又不伦不类贴了个福字的马和,像是在考虑什么,半晌才道:“还是路上再谈吧。”
农历九月末正是黄河秋汛最凶险的时节,从邺城渡河往南,一路俱是颠簸。搅着泥沙的浑黄河水一阵阵地扑上甲板,接天的巨浪险些吞没船只,整个黄河道上几乎不可见普通的渡船,偶尔来往的也只有一搜搜风帆笔直的军船。
午后登门造访的正是史思明长子,其部少主人史朝义。
一开始,李明夷只以为对方是有医疗上的需求,可听到路上两字,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
邺城已经沦为燕土,黄河两岸的交通要塞都被史思明部把持,义军对他们而言已是笼中老鼠。不管怎么说,河北义军于李明夷曾有救命之恩,即便以身犯险,这笔账也该还上。
临行前,他把医署和一应银款全部托付给马和。对方竟没有立时奔向银箱,反倒抹了两把眼泪,做出一脸生死诀别的表情。
李明夷忍俊不禁:“我是去出诊,又不是秋后问斩,道长哭什么?”
马和实在看不出他是在玩笑还是认真,趁着史朝义不注意悄声道:“我刚偷偷替你算了一卦,乃是大凶之象。只怕这一回是劫波重重,郎君自己当心吧。”
“此命由我不由天,信天难,信己易。”李明夷轻描淡写地将对方的话复述出来,徐徐展唇,“不去怎么知道前路如何?”
马和看着他,半晌忽然笑起来:“也罢,这才是马某认识那个李郎。”
交代完家事,带上全套器械,李明夷跟随史朝义一行来到渡口出发。
这回可真是实实在在上了贼船。
到了这会,史朝义才将此行的始末托出:“实不相瞒,陛下眼疾越发严重,所以饬令举国寻找良医,务必为其重复光明。”
说到此处,他顿了一顿,意味深长地添了一句:“尤其是王焘公的弟子。”
听到这里,李明夷差不多也能猜出大半原委了。
王焘是医学史上出名的全能大家,但最让其身负盛名的一点,还是作为开山鼻祖开创了金针拨障术这种白内障手术治疗方法。
白内障是眼科致盲排行榜的第一杀手,安禄山搜罗王焘的弟子,很可能是罹患此病,并寄望于针拨术改善视力。
这种金针拨障术,实际上就是利用金针刺入眼球,破坏其中的晶状体结构,将里面浑浊的物质拨离视轴。
操作虽然听起来粗暴恐怖,由此导致的并发症也不算少数,但对于成熟期的白内障患者而言,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视力水平。所以在唐朝这种手术十分流行,就连大诗人白居易也曾专门著诗记载。
到了二十世纪,金针拨障术已经被完善为一种局麻下的清洁术式,其生命力一度延续至八九十年代。直至人工晶体普及和超声技术崛起,白内障手术有了更安全、疗效更高的方案,这种传承了千年的术式才终于离开了手术室的舞台。
而现在,既没有可以移植的人工晶体材料,也没有优越的超声或激光技术,白内障手术还停留在最原始的阶段。因此,即便是王焘本人也曾一再强调金针拨障术的风险,只将其用于严重的白内障病人,绝不允许弟子滥加施用。
李明夷记得在潼关时,军医长赵良行就曾问过他是否擅长这种技术。
当时几人只以为是闲话,现在想来,恐怕安禄山的病情已经不止一日两日,就连唐军军医都敏感地嗅到了这个可能转折战况的机会。
问题是——疾病会如此单纯吗?
随船渡过黄河便是陈留,有史朝义亲自带队,这一次他们不用绕道。
走过熟悉的城门,街道传来零星的脚步声,不时有唐装的男女远远经过。虽比不得一年前的繁华,但经历数月的修整生息,这座古老的城池也慢慢在安宁中恢复着生机。
相比于数度厄难的河北、胜负未分的关中,这种安宁弥足珍贵。
一行人不徐不疾行经街头,不用拔刀开道,一身戎装已足够让百姓避让。史朝义看着左右空阔的街道,想起什么般问起:“先生要回家看看吗?”
“不必了。”李明夷拒绝得很果断。
此前谢望和林慎已经带来过卢家的消息,从陈留的近况看,史朝义也的确履行了对郭纳的承诺。在民生问题上,史氏父子的作法比安禄山高明不少,也难怪其后能取而代之。
但同行的毕竟是燕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去卢家做客,或许会给几个孤弱女子引起不必要的纷扰和流言。
他给卢小妹一家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只要活着,总归能有再见的时候。
离开陈留的主城后,一行燕兵在驿站换上马匹。马蹄阵阵向国都奔去,金风细雨的水乡逐渐消失在回望的视线中。
根据李明夷的经验,一路乘马不绕行,从陈留至关中大路平坦,花不上半月就能抵达潼关。在有燕兵打头的情况下,应该十日就能达到目的地。
但事实却是,这一路史朝义走走停停,步调悠闲,看上去并没有任何执行任务该有的急切。
或者说,他更像在观望什么。
行至半途的陕郡,天色还未暗下,一行人马就在史朝义的指挥下住去驿站。对此,李明夷当然无甚意见。
夏夜闷热潮湿,晚饭后,驿站里的人稀稀落落坐在门口乘凉。
这回燕兵并没有限制李明夷的自由,毕竟整个河北都已经落入史思明部的爪牙,人质可以万计,绝不怕他半途失踪。
李明夷也坐在台阶上,看星河流转,宇宙仿佛近在咫尺。
他的心情却远不及夜空平静明朗。
就在数百里之远的长安城外,一场攸关国运的战役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如果成功的话,唐军可以顺势收复两京,安禄山只能选择回撤与河北史思明部汇合;可一旦失败……
“长安就要交战。”一道冷肃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史朝义不知何时已经走到门前,同样举首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