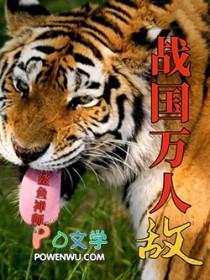葫芦小说>红楼之凤还巢无错字版 > 第407章(第1页)
第407章(第1页)
凤姐顿时跌足:“这么说,他这半年来问我拿了不下千余银子都瞎化了不成呢?”
她母亲王子胜夫人哭道:“何止呢,自你大伯去了,无人约束与他,这许多年来,家里的银钱都叫他瞎化了呢,我都不好说的。”
凤姐替他母亲拭泪:“这话因何不早告我?我也不花那些冤枉钱便宜外人。”
她母亲问道:“这几年你贴他多少银子呢?”凤姐道:“这十几年来,每年约莫千余银子,今年越发了不得,年初要了二百,今天又要五百,我不在,蔻姐儿给了五十,他不满意,这才闹起来了。”
她母亲就哭起来:“真是冤孽啊!亲戚朋友都被他骗光了,人都不愿意跟我们往来了。”
凤姐叹道:“这都怪我们家就他一个男丁,娇惯太甚所致,如今还是想想该如何保住最后的家财吧。”
王子胜顿足道:“而今之计,只有全家回乡,让他脱离这个污秽圈子,当初就不该上京来,唉!”
他夫人言道:“当初是因为他伯父当道,想着他上京求个出身,不想当尽家财,唉,怪的谁来。”
凤姐见父母拿定主意回乡,这才问道:“嫂嫂如何说,侄女儿在京中呢?”
他嫂子甄氏就在外面,满面羞怯进来道:“姑奶奶喝茶,都是我无能,拢不住丈夫。”
凤姐道:“与你不相干,这些年亏得你服侍二老,快些做坐下,我们说话。”
她嫂子道:“无论他怎么想,我都跟着二老,只是我们一日回乡,你侄女儿还望姑奶奶多照应些。”
凤姐道:“这部小说的,现如今家里还有多少财产可动的?你们说与我,我也有个算计。”
她嫂子道:“除了这栋宅子,另外还有两个田庄,拢共四百亩土地,另外就是媳妇嫁妆,我们也没有用媳妇银子的道理不是。”
凤姐叹道:“这些财产,只要兄长不再作孽就在京中过活也尽够了,可是若留在京中,总有一日,他会败光了,难不成他被人砍手砍脚你们不救他?之前财产都不是这样去了呢!”
王子胜之觉得脸面无光,摇头叹息:“都是我教子无方啊!”
凤姐道:“现在说这些也晚了,倘父亲母亲真要回乡定居,房子田庄要如何处理,说个章程,我能帮上尽量出力。”
王子胜道:“房子定要卖掉,否则那个败家子也是赌掉,田庄也卖了,败家子不回乡,我们走了你也别管,让他讨饭吃。”
凤姐道:“放任不管也不好,我虽恨他不成器,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没下场吧,错不过血脉相连呢。这样吧,我让你们姑爷去寻他,将他送回家来,两老好生与他说说,倘不听,捆也把他捆回去,人手我派,您们看着可好?”
王子胜夫妻都道:“就依你。”
凤姐起身告辞:“是不迟疑,我这就回去,怕晚了,他又输个精光了。”
王子胜夫妻之抹泪,王仁夫人把凤姐送出门,她儿子媳妇一边脸红耳赤,只给凤姐道恼。
凤姐回得家来,贾琏已经到家,正在喝茶,逗着贾萏,凤姐回家把那事儿一说,贾琏顿时垮了脸:“这叫我如何下手,随他去,贴几个钱就是了。”
凤姐也垮了脸:“我兄长刷不成器,你恨他我不怪,可是我爹娘伯父待你不错吧,你就忍心看他横死街头?你就不为我爹妈考虑,侄儿们考虑,不为我考虑,也该为巧姐儿、葳哥儿想想吧,有个作奸犯科的母舅,只怕好听呢,葳哥儿要出仕,巧姐儿将来做王妃,安王府里那些个庶子大眼贼似盯着,就盼着巧姐儿有什么把柄才好,救我于你没好处,巧姐儿葳哥儿不是你的骨肉?你就忍心不管呢?你怎么这么狠的心?”
凤姐这一拉扯,贾琏坐不住了,忙丢下茶杯,放下萏哥儿:“你这说些什么乱七八糟呢,我去,我去还不成呢,来人,备车。”
凤姐这才抹了眼泪,忙着替贾琏穿衣服递帽子,整理衣襟,贾琏见凤姐抽抽噎噎,忽然一动,伸手摸一把:“这个婆娘,越老越火辣。”
凤姐一瞪眼,嘴一努萏哥儿,平儿忙把萏哥儿抱走了,凤姐啐一口:“德行,儿子面前也要庄重些。”
贾琏直乐,顺手在凤姐脸颊一掐:“小孩子懂什么,我这就去,你在家里把酒烫好了,炒了小菜等着啊,不然,看我如何收拾你!”
凤姐斜着眼睛把他推出门去,自己摸摸脸倒笑了。
结果,凤姐把酒温了,小鸡子炖了,贾琏却没回家吃饭,天擦黑才回来,原来王仁不就范,贾琏拉不下脸动手,前几天还一起喝酒呢,委实翻不来脸,只得智取,请了王仁喝酒,那家伙酒量还不小,等把王仁唬弄回去,贾琏也高了,嗳哟,不是彩明搀扶着,连门也找不着了。
别看他醉得一塌糊涂,凤姐账还记得,看见凤姐就一扑,结果扑到了凤姐,他自己倒呼呼睡着了。
凤姐翻下身上贾琏,直乐:“这个醉猫,平儿,块来。”
平儿抿嘴直乐:“我看着倒不是醉猫。”
凤姐笑道:“那是什么?”
平儿一挑眉:“老色猫!”
凤姐扑哧一笑:“这倒确。”
妻妾一边埋汰贾琏,一边收拾服侍他睡下了,隔天早起,贾琏想起,到底找回了后账,差点误了早朝。
却说这一日三月十八,王仁儿子王玉林来了,王子胜把王仁腿打断了,如今王家也不能传太医了,恳求凤姐帮着请个跌打太医,好好治疗一下,免得落下残疾。“
凤姐忙问:“如何就腿打断了,怎不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