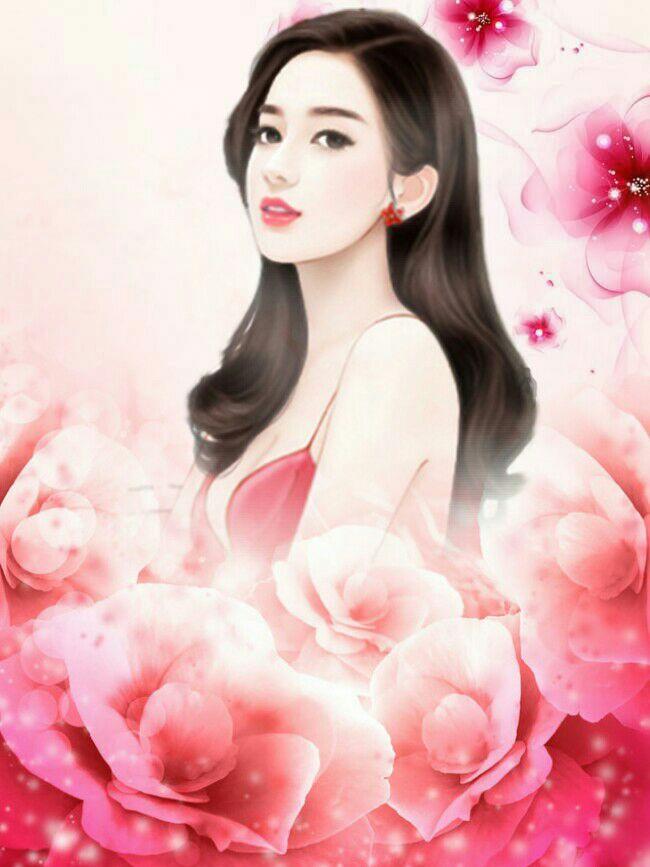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歧途:我一生的岔路 > 第四十三章 重逢(第2页)
第四十三章 重逢(第2页)
“将就。”
金琬脱口而出,掩口而笑。同时怕再遭“报复”似地站起身来,绕到书桌旁边坐下说:
“说实话吧,你这人不仅具有相当的素质,气度和气质也很好。人严肃、精神,气宇轩昂,堂堂一表的,给人一种浩然正气感。只是,每当你处事认起真来,或心情不好时,神情有嫌过分庄重严肃。另外,你遇事常是得理不饶人,甚至是霸道、霸气……搞起来,好像煞气很重似的,凛然难犯,叫人生畏。”
“噢,这样不好。”卯生由衷地说,“感谢提醒。这德性,我力争着改。”
“还是算了吧。生成的禀性,改也有限。再说,严肃也不是不好。孔子不也说过‘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吗?只要为人正直、庄重,给人的是敬畏,严肃人办事效力高。不过霸道、霸气方面,能改还是改一些的好。”金琬说着,又浅浅一笑:“有时候我在想,按你的气质和才识,倒真是一块做官的料哩。难怪总有人看重你。”
“笑话了。”卯生苦苦一笑,“如果真如你所说,我也只是空有其表,苦无其命;白让我的伯乐们枉费神思、徒费苦心了。唉!”
“看看,又惹你伤感了。”金琬起身倒杯水递给卯生说,“闹腾了半天,现在该说说你在外面的情况了吧。”
“还是先说说你吧。”卯生坐在床沿上说。
“我有啥说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吃饭挣工分,挣工分吃饭。只是感觉到人很累,远没有你在家时的那种舒坦、娱悦的心情。”金琬叹了一声,又说:“再就是很想你,心中总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令人忧伤中没道理的总想哭。”
卯生拉起金琬的手,像安慰似地焐着,相互都沉默着。他从金琬冰凉的手上感到了冷,便起身掀开被子,拉她双双相依相偎地坐到床上,四只脚互叠互放于被子里。这样暖和了许多。
他又问起她母亲的情况。她说她母亲九月里害了一场大病,好险去了;病后人衰败了很多,至今难以复原,随时都有可能再发病。
卯生听到此,不禁心中一动。他明显感觉到了这是高兴。同时也考虑到了这种高兴的不道德。但又深深感觉到这是本能的,下意识的,近乎不受人意识支配的。
这霎时,他体验到人是双重性的,善良与残忍并存,博爱与自私互在,选择、使用它的只是人的理智。
他为掩饰过错似地搂紧了金琬。
金琬又说,今年九月是个不幸的月份,母亲的病刚刚轻松一点,河马家又来捣乱。河马请人劝说金琬,说是要求重圆旧好。并说如果她答应了,就可以到大队小学去教书,教书就有可能转正吃皇粮。还说,河马已经决定让他儿子今年冬天去当兵,因为当兵回来就好谋工作。那样子,他们将来就都可以跳出“农门”;那样子……他们设想的未来小两口,这一辈子的日子就好过了。
卯生静静听着。他心想,河马那痞子想得的确算周到。而且,凭他现有权势和心眼,这两件事他都能稳操胜券,完全可以办到。当金琬的话停下时,他紧张地追问:
“你答应啦?”
金琬瞪他一眼,道:“答应了,还能同你在一块?答应了,不是已经教书去了么。”
“那,”卯生尴尬,“你是怎么答复他们的?”
“你想,我会咋答复?不,如果调个位置,你是我的话,你会咋答复?”
卯生不假思索:“我会骂:做梦去吧,狗娘养的东西!”
金琬一笑道:“你呀,骂起人来,总忘不了那一句‘狗娘养的’。”
“咋,粗俗,下流?”
金琬含笑摇头:“粗俗下流倒不全是,但也说不上文明。不过,你说话从来不带脏字——我说的是那些不堪入耳的脏字——与那些满嘴臭气的粗人相比,你倒还像个知识分子。”
“还像?劳驾你抬举了。”卯生笑道,“还是言归正传吧。我若是你,我就答复他们:‘对不起,我已经将终身许给何卯生了!至于你们,算不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姑且不论,但人总该有些自知之明吧,还是回去自我掂量掂量的好’。”
金琬依然含笑道:“眼下我还没有这个胆量。如果具备了这个条件,也许我会说出你那前半句话的。我当时回答他们说:‘过去的事情,纯属开玩笑,不存在啥“旧好”。开玩笑的事早已结束了。这一辈子我不敢高攀、也决不高攀。下一辈子再看造化吧’。”
“说得好!不过最后一句话不该说。因为下一辈子你也应该是我的,或者说我是你的。”卯生**地搂着金琬的肩头。他无限感激她。他想,作为农村姑娘,作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者,如果不是金琬,也许没有几个人经得住河马许下教书职业的诱惑。由此他想到自己,想到了自己和金琬的未来。倘若自己将来混不及人时,如何对得起金碗这片痴情忘我的情义?
为此,他又想起王处长的话,心中升起无限希望。若果一切顺利的话,别动队一旦收归“红星”,他相信自己立即就会调到基建处。因为王处长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红星”现在只是筹建,一旦大规模开始兴建,一个新兴城市,一个重工国企的兴建,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基建处是他大有可为的用武之地……他想他的前程是美好的。于是,他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了金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