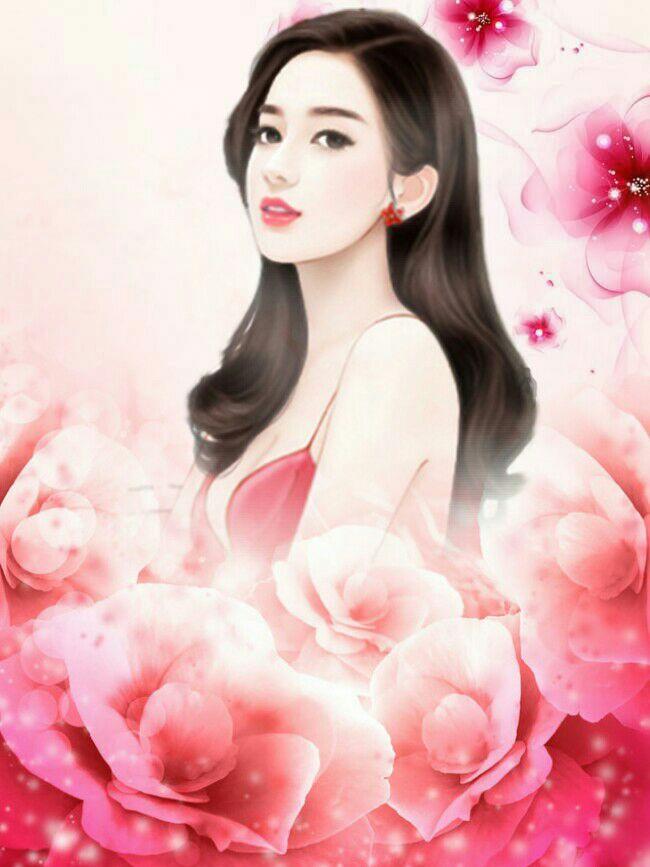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歧途:我一生的岔路 > 第二十六章 慈母病重(第1页)
第二十六章 慈母病重(第1页)
卯生终于为母亲做了一套新衣服。只是高兴中含有一缕遗憾。由于钱的关系,他没有买到最好的布料。这年代,值得一说的布有三种。第一是人称的“卡叽”布,一元左右一市尺;第二是斜纹布,六毛左右一市尺;第三是平板布。卯生买的是五毛七分五厘一尺的蓝色斜纹布。这布还算厚实,只嫌布面上的“斜纹”较粗、较松,而且蓝色中有些微微泛紫。不过母亲很高兴。他抚摸着卯生的手,无限感概地说:
“我真有福气呀,终于有儿子为娘做衣裳了。”
这话,这声音让卯生记了一辈子,既甜又酸,多时还无端下泪。
那件事更让母亲高兴的是,卯生将挤出的钱,为惊蛰买了一段削价处理的平板布头儿。她当天裁剪,为她幺儿惊蛰做了一件上衣。只有玉珍老斜着眼睛不高兴,这年春节,她像卯生一样没有新衣服。
卯生守口如瓶,对谁也没提起向金琬借钱的事,反吹牛说钱全是他攒的私房钱。他想让母亲穿得心里踏实,穿得舒服。
楚天家这个年过得还算可以。粮食虽紧,但有秀章奉信的“穷月丰年”的平日节俭,过年粮食已不是问题。已分家另过的贤昆,不知从哪里买了两斤猪肉送来,又凭添几分喜庆。酒,早在卯生砍柴为父买酒时,秀章就悄悄留下了两斤。楚天有酒分外高兴,全家人也就跟着高兴。比物资更珍贵的,是一家人和睦团聚的愉快气氛。这个年是值得卯生怀念的。
只是过年时侯,卯生心中暗自有一丝隐痛,因为母亲没有穿新衣服。母亲说是等开春后,脱去棉衣时再穿新衣服,那样人会更精神一些。实际卯生心中明白,是新衣服有点短,套在外面,露出了里面棉衣半寸长的的红脚边,为人留下遗憾。买布前他问过母亲所需尺寸。不知是母亲惜钱让他少扯了布,还是裁缝心黑贪污了布料。反正他心里不是滋味。他暗自发誓,明年一定多买两尺布;而且,天难地难,天塌地陷,也一定要买上最好的布。
正月初三下午,卯生便约齐冬娃子、长娃子等人,相议明日初四开始砍柴。他急于要还药铺尹先生和金婉的钱。欠人钱,心中日夜不安。
“不行吧?明天河堤上开工。”长娃子厚嘴唇艰难地启合了两下。
冬娃子也抽抽鼻涕:“开始就耽误,行呀?”
卯生说:“能利用的就是‘开始’。”接下他条理清晰地分析说,“三治”工地不是生产队,它是几个大队加在一块的大家伙。几千人一体,年后开工的头好几天时间里,一定是人齐马不齐;各项规章制度也有重新调整的过程,所以他料定这开始一段时间,其奖惩制度一定不甚严格。此空不钻,更待何时?
大家恍然大悟,一致赞同卯生的分析。于是卯生等人又到了久违的将军岜,而且一直砍过正月十五。结果,一切都在卯生预料之中——河堤上的奖惩制度,不偏不倚,正好从正月十六日起实施。真是天随人愿。
卯生正月十六到工地,依然拉泥船。但只做了两天活路,母亲突然又病了,而且病情来势凶猛,只一天,母亲便卧床不起了。这阵势,令全家紧张,楚天更急。他让卯生立刻去请甘伯勋。一诊脉,伯勋先生便沉沉地摇头道:
“唉,人太衰弱了呀。”
卯生一惊:“要紧不?表伯!”
伯勋看看卯生,摇头道:“不好说哟。”
楚天问:“你看她是不是加有新病?”
“没有。还是老毛病。只是人太虚太弱,中气严重不足。”伯勋低沉地叹一声,道:这次……你恐怕要早作准备呵。这人,随时都有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卯生急叫:“哪就补啊,表伯!”
伯勋对卯生说:“好娃娃,我晓得你的心,可盛虚不堪补呵,你母亲这身体……已经经不起一补了。”老先生说了很多医理、道理,卯生听得似懂非懂。最后在他一再的哭求下,伯勋答应竭尽所学,尽力而为。
卯生赶到药铺,将正月初四至十五的十二挑柴钱,一分不留全部交给尹先生,并说明原委,要求先生格外开恩地再度赊药。慈眉善目的尹先生道过几句苦衷,接着居然苦苦含笑道:
“咋办呢,百善孝为先,孝心可感天和地呀。在你这个大孝子面前,我咋能做缺德的事情,咋敢不赊药呢?赊几剂吧。”
从此,卯生每隔日来一次,一次两剂药,一连多天,尹先生从没拒绝过。可是一天天过去,母亲的病不仅不见好转,反有日渐严重的趋势。这令他焦虑不安,心急如焚,时常暗中哭泣。
卯生看得出,母亲的病痛仍然只是咳嗽,堵气,喘,没有新加什么病状。只是正如医生所说,人的确太虚弱,没有力气供应咳和喘的需要。以致她喘时扯不起气,咳时送不出痰,常常为此憋得面色惨白,痛苦不堪。其情形让人看得心痛万分,又深恨自己替代不能。母亲十分坚强,无论多么痛苦,她从不呻吟,从不叫苦,显然是怕家人为她担心。
母亲内心一直是很明白的。她不堵气时,面容一如平时,也并非十分消瘦,依然那么慈祥端庄。每平静时,她总无限依恋地拉着卯生的手,由浅及深,由轻到重地教他做人的道理,流露着对他个性的担心。从母亲交待后事般的言谈中,卯生日盛一日地预感到了不祥。他不敢想及母亲会死去,却又无法控制不去想。在他想象中,倘若真有那一天,真有一天失去母亲时,那境况定是这个家庭的世界末日,一切都将随之崩溃与坍塌。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卯生于心目深处有种切肤的体会:母亲是这个家庭夏日里的一片绿荫,是冬天的一盆火。母亲用她的善良与精明呵护着这个家,凝聚着这个家。因为有母亲,无论时局与生活多么艰难,多么困苦,这个家所有成员都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希望感,同时也都在享受着家庭天伦之乐中的温馨和幸福。
而现在,面临母亲有可能随时离去的严竣时刻,家庭即将失去顶梁柱的时候,卯生更是深深感受到了已经过去的时光是多么珍贵,多么值人留恋。他想到了一个家庭能否兴旺,有无前途,不是有无一个两个壮劳力,而是有无一个精明人,有无一股凝聚力。而如今……这个家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何况,他是多么需要母爱啊!
自从母亲卧床之日起,卯生仅是头三天没有上工地。第四天便在母亲劝说与催促下,他又拿起了拉泥船用的麻辫子。她知道母亲在为这个家庭着想,更知道能挣回几分工票和半斤毛谷子,对穷怕了的母亲是一种莫大安慰。可是,他是那样的不忍离开母亲。因为伯勋先生说过,母亲随时都有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他担心,也不知道此去回来时,还能否再同母亲说句话。他每临走时总是强忍眼泪,磨磨蹭蹭,一步三回头地力争多看母亲几眼;常常是人到大门口时,又忽然转身跑回来再看母亲一眼。心想,但愿这不是最后一眼。
他哭着跑着,走捷径直下彭家大院子,跨过七星桥,穿过大坝田,飞奔工地。一到工地,他便独挂一架泥船,一人拼命地拉上石场,拼命地抢石头,然后独拉一船直奔河堤。这样可快许多,四人拉一船,一般顶多是五分工票,一人拉一船,至少顶多都是两分。只是人很苦,没人肯干,也不被允许,因为危险。可是卯生此时顾不得许多了,他要快,要争分夺秒地朝回赶。“也许哪次慢一步,再也喊不应母亲了”。
他总这么哭一样低声警告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