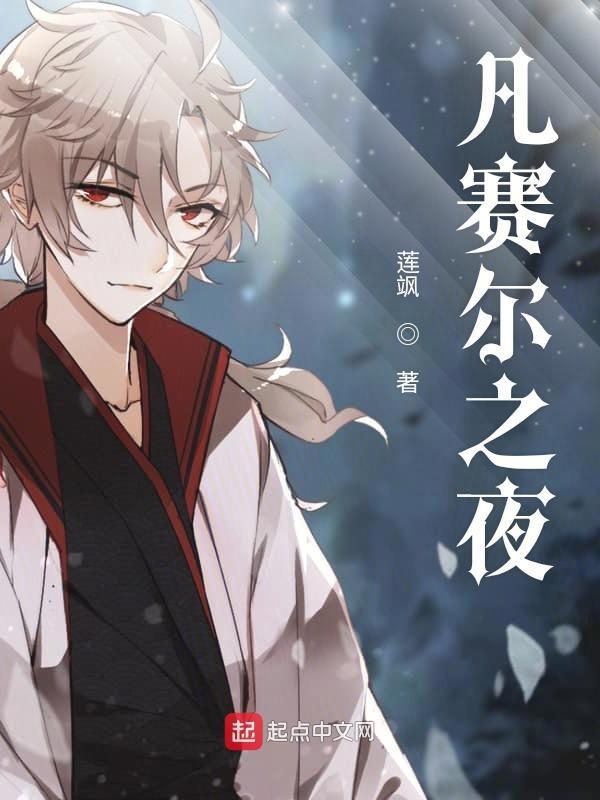葫芦小说>朕真的不务正业 > 第689章 论奸臣的自我修养(第3页)
第689章 论奸臣的自我修养(第3页)
但王崇古认为臭不可闻。
王崇古将杂报放下,摇头说道:「这篇杂报的内容,是错误的,不了解住坐工匠制度导致的,陛下,短工其实不省钱,尤其是对官厂而言,除了图个方便,臣想不到别的原因了。」
「不省钱?」朱翊钧一愣。
「陛下民坊离了熟练工匠顶多生产点附加价值低的商品,官厂不行,官厂要只能生产低附加值商品,还怎麽占据主导地位?怎麽当得了主心骨?真的不省钱,熟练工匠创造的利润,是一个学徒的十倍甚至更多。」王崇古首先纠正了下陛下的偏见。
临时工真的不省钱,对官厂尤其如此。
王崇古接着说道:「不事生产的人,往往都这个样子,他们从来没见过官厂里的工匠,就是五级匠人里最顶级的大工匠,都是闲不住的人,你不让他们干,他们还要骂人呢,总想捣鼓点什麽,就跟这些读书人一样,肚子里有了墨水,怎麽可能不写点什麽?」
「官厂里,当然有大搞特权的人在,但匠人们玩的花样,可远不如这些读书人搞出来的这些东西,啧啧,也不知道这笔正,是怎麽好意思说匠人们大搞特权的。」
「贱儒的眼里,整个世界都是下贱的!」
这个笔正大肆宣扬的问题,在官厂当然存在,但最大的问题,近亲繁殖,大明本身就是世袭匠户制度。
「陛下,匠人在官厂里占到了主导地位,这是贱儒所不了解的。」王崇古思前想后,还是要对陛下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匠人们不服大把头,不服这些官吏胡说八道,是可以表现出来的,甚至是可以指着鼻子骂这些官吏多管闲事,我儿带着笔正去毛呢厂看铁马的时候,就有法例办的人,让王谦把帽子带好。」
「官厂是搞生产的,生产就是如此,各管各自的事儿。」
「住坐工匠之所以如此胆大包天,甚至敢为难王谦,而王谦也没办法,只能把帽子带好,因为住坐工匠的逐出,是不被官吏所控制的,而是由法例办调查清楚事情原委后,送到总办手里,如果涉及到了刑名,就会移交衙门,如果不涉及刑名,就会酌情。」
「陛下,住坐工匠是官厂的固定资产,是原料变成商品,变成钱的资产,没有刑名之罪,是不允许轻易革除住坐工匠的。」
住坐工匠和民坊里的工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是贱儒们所不清楚的。
大明官厂是存在新陈代谢的,官厂的代谢名叫清汰,制定的考核标准多次无法完成丶多次违反安全生产条例丶重大生产事故,以及政治清汰,就是官厂的新陈代谢,但官厂的人事总体上比民坊稳定。
考核标准是五级工匠里该级工匠最效率的匠人的七成,而徐州煤窑在私人手中掌控,往往是以最高效率再额外添加工作量进行考核,能完成才有鬼。
而考核的话会有六册一帐,官吏是无法随便为难匠人的,匠人手里有自己的帐,工坊有自己的帐,厂里也有帐册,出厂也有帐册。
这都是官厂建设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
这里面让王崇古最痛心的就是政治清汰了。
之前有青楼女子从良投奔官厂后,有组织的利用官厂的背景,自己织娘的身份,四处骗婚,自那之后,青楼女子,就不得入官厂,南衙有青楼女子从良,就差一天,没能进了官厂,最后吊死在了织造局门前,但依旧没有改变这个政令。
而这个政令还有后续,更加变本加厉了起来,青楼女子出身的织娘,考成都会比别人更加严格一些,更加容易被官厂清汰。
织造局丶毛呢厂的青楼出身的织娘,很多都已经是熟练工匠,在政治清汰中,损失严重,不是所有青楼女子,都是自愿踏入那烟花世界的地狱之中,但官厂对她们关上了大门的同时,已经上岸的青楼出身的织娘,也遭到了牵连。
「管理官厂,辛苦王次辅了。」朱翊钧对王崇古进行了夸奖,是真的辛苦。
「陛下,臣老了,王谦呢,又对这些不感兴趣,整天泡在那个交易行里折腾,赚的钱比臣还多,臣其实也担心臣死了,这官厂后继无人。」王崇古有些感慨的说道。
海瑞不搞王崇古是因为离了王屠户,陛下真的要吃带毛猪。
官厂是国之大计,这个位置,离开了王崇古,一定会有巨大的变动,势要豪右们刺杀王崇古是对的,官厂是因人成事。
当初的毛呢厂,不过是为了羊吃人,削弱北虏的实力,慢慢的才发展到现在这种规模。
王崇古甩了甩袖子,拿出了一本奏疏说道:「臣总结了官厂管理的若干办法,形成了法例办,但这法例,也要因时而动,不能墨守成规,否则僵化之下,官厂不能长久,臣思来想去,还是写了一本奏疏,恳请陛下过目。」
朱翊钧看完了王崇古的奏疏,面色颇为严肃的说道:「大明工匠,都要谢谢王次辅,不仅仅是官厂,整个大明的官僚,也都该读读这本《官厂法例诸事疏》。」
这本奏疏不仅仅是讲怎麽管理官厂,而是讲怎麽当官。
总结起来为四句话:
对群体保持同情和关注;对个体保持警惕和距离;
严格按照制度和流程办事;事事处处都要留痕迹。
这四句话道尽了官厂管理的纲常,同样也是在说如何当官,要具体展开说,就非常非常的复杂,大抵而言,就是群体的诉求一般情况下都是合理的,但个人的诉求通常都是谋求特权,这是人性的必然。
制度和流程虽然僵化,但同样也是保护自己,每一件事都要留下痕迹,最好有文书为证,防止在宦海沉浮的时候被敌人抓到把柄。
能把这四句话做好,就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了。
「陛下谬赞了。」王崇古起身告退,他的脚步非常轻快,而且非常稳健。
朱翊钧拿着手中的这本奏疏笑着说道:「王次辅怕是看到了傅希挚的下场,才有感而发,写了这本奏疏,这本奏疏要是改名为《论奸臣的自我修养》,恐怕会引发竞相追捧。」
王崇古既然把奏疏给皇帝陛下,陛下是拿去发在邸报,还是拿去刊发,他王崇古都懒得管。
朱翊钧打算把奏疏的名字改一改,吸引大明官僚们都阅读一下这本书,以防止自己被权力异化,最后锒铛入狱。
「这麽改,是不是太伤王次辅了?」冯保眉头紧蹙的说道,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王次辅现在又不是个奸臣,这麽说,伤大臣的心。
朱翊钧摆手说道:「你说得对,他可以自己说自己,但朕不能这麽说他,现在王次辅忠君体国丶经邦济国。」
「不如这样吧,改名叫《论五步蛇的自我修养》,这五步蛇可是王次辅亲自认可的绰号。」
「臣遵旨。」冯保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后面这个名字更好听点,同样还能通过宣扬五步蛇的威名,以收威吓之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