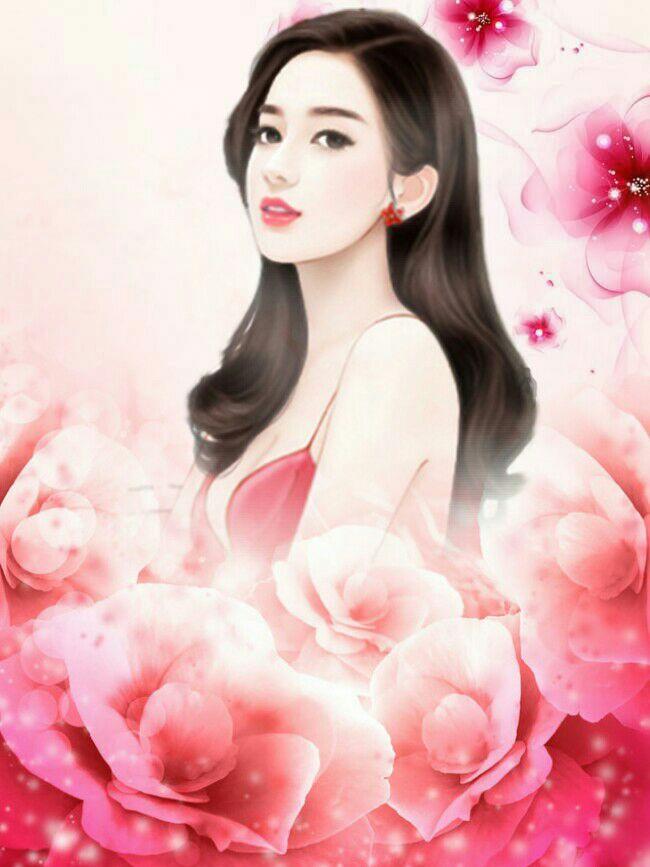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被敌国将军当成白月光后 > 第289章(第1页)
第289章(第1页)
>
去年她的生辰,小郎君雕了柄木质匕首给她,连说抱歉只因他买不起铁打的匕首。她却很开心地收下来了,从此一直别在腰间。
不曾料,十五岁及笄那年,她没等到小郎君来提亲,却等来了他从军赚取军俸的消息。
离别那日,他头一次握住了她的手,紧张到掌心汗湿。他说,等他赚够了钱,搏一搏军功,就来娶她。请她,一定要等他回来。
她当时重重点了点头,应下了。
可而后,她也被父亲送入宫中,背井离乡,本是满载着家族的期望,却因容貌平平在宫中只得了粗使婢女的活计。
从此,她再也没望过天。皇宫里只有四角的天,无法与故乡的天相比拟。
而她的故乡,已变成了她遥不可及的回忆。
凉州离长安,有多远呢?
她当年从家中出发,跟着马车走了数月才到长安。入宫后,每年通过驿站往家中寄信,要次年才能收到家人的回信。
但她听她的好友,御前伺候的小梁子说起,长安与凉州往来军报最快仅需十日便可送达,只不过得跑死数匹良马。
风荷记得小梁子说起那话时吹嘘的模样,她才不信有那么快呢。小梁子向来喜欢夸张其词,故意逗她玩。
小梁子是和她同一年入宫,却因肤白貌美,人又机灵,进了内侍省,认了掌印张公公作干爹,也讨得了御前侍奉的好活儿,从此平步青云。
他发达了,却从未忘记风荷,还会时不时送她些有趣的玩意儿。
虽然有的是人要讨好他们御前的人,过他们手的一般都是贵重的物件,但风荷也不怎么稀罕。她只喜欢公主赐下的东西。
公主向来大方,会把逢年过节宫里赏赐的绫罗绸缎赏给她宫里的人,由凝燕姑姑往下分发。
凝燕姑姑是朝露宫的掌事姑姑,听说原来是另一位和亲在外的长公主的侍女,只是不知为何又回到宫内,侍奉起了这位清河公主。凝燕姑姑素来板着脸,从来不笑,眼边还有道刀疤,风荷起初是极怕她的。
但接触久了,倒觉得她为人刚正,行事公道,就像这次中秋,大家选赏赐的时候,凝燕姑姑就指着她说:
“风荷值夜从不打瞌睡,该赏。这些公主赏赐的布匹,你先选。”
她又惊又喜,被推搡着出去,欢天喜地挑了一匹赤色罗纹的绢布。那么好的料子,摸起来像幼儿的肌肤一般柔软。她想存下来,等她年满出宫后,她的小郎君也该从军中回来了。
到时候,可以裁作嫁衣。
姑娘家,谁不喜欢红艳艳的呢。可公主殿下的衣裳一向寡淡,白得就像故乡天边的流云一样。自风荷来她宫里,从未见她穿过红。艳色的布匹都被作为赏赐,倒是便宜了她们这些下人。
可即便是发赏赐的时候,也从不见公主人影,都是由凝燕姑姑代劳。
公主甚少出门。若是出门,便是去含元殿。小梁子偶尔说起过,公主和圣上谈的,都是西北的军机大事,不要他们伺候,连他和他干爹都会被屏退在外间。
风荷就想,怪不得公主每次从那里回宫,都是眼见的疲累不堪,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精气神。
她印象最深的一回,公主刚过晌午就急匆匆离了宫,从含元殿回来时已是入夜掌灯时分。
公主被凝燕姑姑搀扶着回到朝露宫,在门旁守着的风荷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面色惨白如纸,鸦青的鬓边已被湿汗浸润,发青的唇一张一合,虚弱地笑着,正对身旁的凝燕姑姑说着些什么。风荷只隐约听到一句:
“还好,还好圣上被我劝下来了,没有听张恪的。”
风荷也曾听说“伴君如伴虎”,越发佩服起小梁子他们的本事儿来了。
若不去含元殿的时候,公主平日总会待在暖阁书房里,整日都不出来。
暖阁的书案上,终日摊着一张黄麻纸为底的舆图。
那是公主的宝贝,从不让任何人动的。
风荷只记得有一次,她替班进去洒扫,见到公主趴在舆图上,柔白的面靥紧贴着粗糙的纸面,纤细的玉指轻轻抚过舆图上一个个乌黑的小点。
温柔得,就像在抚摸爱人的面庞。
其中一个她手指盘桓最久的黑点,上面的字迹,风荷识得的。
正是她的故乡,凉州。
彼时的她并不知晓,公主和她一样,想极了凉州,想要回凉州。
她只会羡慕公主,金枝玉叶,锦衣玉食,深受圣宠,只要她蹙个眉,想要什么,内侍省都会巴结地即刻送来。
可公主她偏偏什么都不想要,终日在房里待着,守着那份舆图,空洞的眼神盯着舆图上的凉州。
风荷想着,许是公主身子不好,没有兴致,待她好些了,就会开心起来了。
公主身子一直不好,风荷是隐约知道的。
因为那个眼熟的太医每月都会来宫里看一次。每每他临出门,风荷都会观察他的神情,是一回比一回凝重,到最后干脆哀叹连连。
彼时她只是有猜测,却不知道到底有多严重。
直到那一日。
不过才入秋一月,皇宫里却是已冷得直冻脚。风荷本是守在朝露宫门处值夜,忽听寝宫里传来一阵惊呼。
她奔了进去,赫然看到素纱帐幔之中,掩着一大片鲜红,在烧灼的烛火下显得煞是触目惊心。
是公主睡梦中突然醒来,大吐了一口血,再昏死了过去。
朝露宫乱作一团,风荷从未见到一向有条不紊的凝燕姑姑如此慌乱的模样。
那夜,圣上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