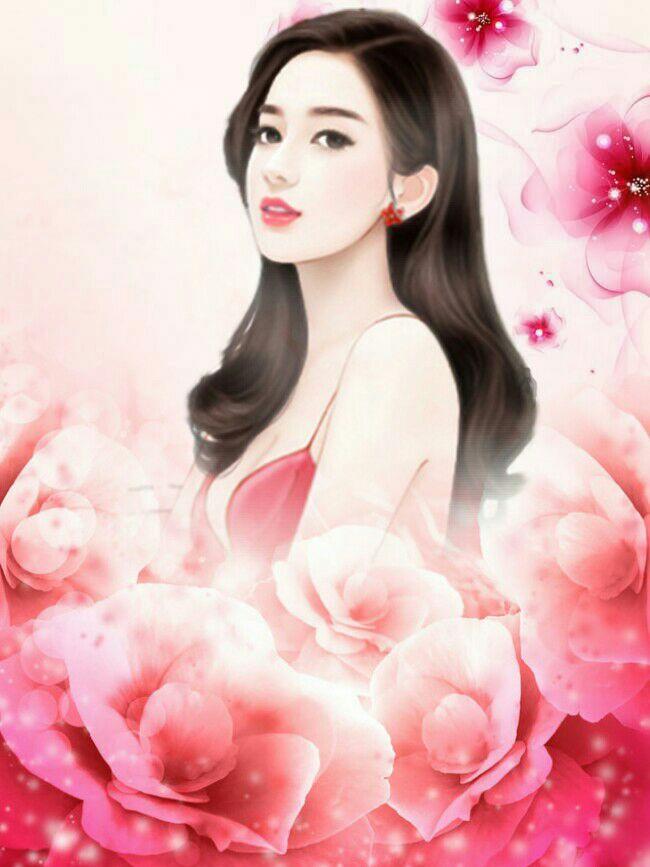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被敌国将军当成白月光后 > 第215章(第1页)
第215章(第1页)
>
风起云涌,暴雨将至,凉州城内人影稀疏。
凉州都督府前,匾额侧边高悬着的两盏灯笼,内里幽幽烛火被风吹得黯然无光,摇曳间几近熄灭。
一名男子疾行的身影从街角中窜出来,一身青灰衣袍被暮色泅染得色泽更深,凌乱的脚步一级一级踏上血迹未干的斑驳石阶。仅有的一只手一下又一下猛扣着府邸紧闭的大门。
朱漆色的门扉如血色浸染,许久才“嘎地”一声,开了一道小口。
司徒陵从狭小的门缝中奋力跻身进入,不顾一众阻拦的玄甲护卫,直接拔剑而出,一路猛冲,强闯入府中的主厅,一面高喊道:
“萧长风,你给我出来。”
厅中一面舆图前,正与众将议事的高大男子缓缓回身,锋利的目光扫了一眼来人。对身旁的众人淡淡令道:
“都先下去吧。”
众人得令,噤若寒蝉,默默退出了正厅。养宁远最后一个退出前,与疾步入内的司徒陵错身间,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小幅地摇了摇头。
司徒陵看见了他刻意的警示,心下更沉,仍是举步朝前。他紧紧跟上已快步向厅后书房走去的白袍男子。待他后脚步入后,书房雕镂的双扇门立即被侍从掩闭起来。
房内的光一下子收束殆尽,日暮的斗室暗沉如夜。
片刻,一小簇微茫的火苗燃起,照亮了黑暗中男人寒凉无比的面容。火光缓缓移向一侧,点在了案上的烛台。
房内倏然亮堂起来。
司徒陵望着男人坐在案前,漫不经心地用修长的手指拨动着渺小的烛火,好似在玩弄。火光在他手中来回摇动,房内的暗影随之晃动不已。
司徒陵深吸一口气,道:
“你与陇右崔氏的新仇旧恨与我司徒陵无关,我无意干涉。但崔焕之怎么说也是一方主帅,你怎可将他囚禁折辱至此?”
见他沉默不语,面容浸在烛火明暗不定的光中,鬼魅一般摄人,司徒陵抑制着心中寒意,不禁上前一步,低声道:
“可清河的魇症……”
“够了!”长风低喝一声打断了他,手掌握紧了木椅髹漆的把手,像是要将把手上的恶蛟镂雕一掌捏碎,厉声道,“你又要用她来威胁我?”
看到司徒陵满目错愕,他的嘴角浮起一丝轻蔑的笑,冷冷道:
“她让我不要攻城,我照做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夺取本就属于我的凉州;她让我放过城中百姓,我照做了,夺城前后民生分毫未伤。我已把一切做得悄无声息,凉州城内巨变,不会为外头察觉一丝一毫。你们还想我怎么样?”
司徒陵被他的目光盯得汗浸鬓角。
这几日,他司徒陵虽驽钝,也看出了一些端倪来。
他此举极尽巧妙,不费城外回鹘玄军一兵一卒,只动用了城中当年残留的河西余军,未曾私通外敌,只能算节镇之间稀疏平常的抢地兵变,已算不上谋反大罪。朝廷素来对此睁一只闭一只眼,长安的圣上甚至都巴不得节镇互相倾轧,掣肘之术罢了。
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萧郎妙计,不攻不伐,笼络旧日人心,出手狠准,几日内将凉州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
这位归来的萧郎,深谋远虑,杀伐果断,更甚从前。
他的这番局,不像是几日之功。只是不知,他已为此筹谋了多久。
司徒陵心下叹服,但又念及那位为此心力交瘁的女子,犹疑道:
“她今日吃不下饭,突然问起了崔焕之。你让我怎么答?”
“凉州本就隶属我河西萧氏,百年基业,都在此地。此城,我夺得理所应当。至于崔焕之,”听到这个名字,男人目色沉了下来,冷笑道,“陇右军已为我军俘虏,他不过我手下败将,胜败本就乃兵家常事……”他轻抚着座椅上凹凸不平的镂刻,恨恨道:
“要怪,就要怪他崔焕之当年,不该贪我河西的残军,妄想他们归心。今日,倒为我所用,被我反将一军。”
他在火光中扬起头,紧绷的下颌线像是一道出鞘的利刃,重重道:
“我和陇右崔氏之间,不仅是兵家之争,还隔着两军宿仇。这一切,根本与她无关!”
“与她无关?”司徒陵咬牙道,“你可知,陇右军中那些今日被你策反的河西残军,包括养宁远,本是清河当年亲自以公主之身求陇右崔氏收留的。是她不想你的兵变为西北的流民,苦苦哀求着崔焕之纳入麾下的!”
“你如此行径,她若是知道,该如此自处?该会有多痛心?她在陇右军待了五年,深受军中将士照拂,与崔焕之更是相交多年,情谊深厚。你对陇右军痛下杀手,可有考虑过她的感受?”
男人从手中的烛火前收回目光,掀起眼皮,逼人锋芒从他黑沉沉的眸中射出。只那么一道暗沉的目光,竟令司徒陵心间一震,不由后退了半步。
“情谊深厚?呵——好一个情谊深厚!”他遽然拍案而起,高大的身姿将案前的烛火全然遮住,衬得他暗光中的面容愈发阴郁难测。
他静了片刻,动了动喉咙,像是忍耐下了汹涌的情绪,沉声道:
“待我肃平一切,我自会向她交待一切……”
司徒陵微微一怔,叹了口气,继续道:
“可她本就是局中之人吶。近日来,她的魇症迟迟未愈,气色一日比一日差,我担心,她知道后更是……唉……”
男人眯起幽深的目,一字一顿道:
“既如此,那便继续瞒着她!瞒到我大仇得报为止!”
她可瞒,为何他就瞒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