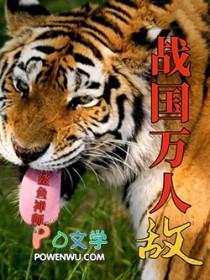葫芦小说>渣了仙道第一人+番外 > 第2章(第1页)
第2章(第1页)
雨声传入屋中,许是因为下雨,气息都带上了凉意,屋子角落中摆着几个瓷碗,碗中还有半碗水,此时有雨水从屋顶滴落就落在碗中。
温疏晏有些浑浑噩噩的醒来,耳中都是屋外的雨声以及屋中的雨滴声,思绪有些混沌。
下雨了?
他这么思索着,喉咙干涩好似火烧一般,下意识转头去看床边。
那儿摆着个小凳子,凳子上是一碗水以及一瓶药和纱布。
喉咙的干涩也更加的厉害,不由得咽了咽唾沫,他才缓缓起身想要去拿水。
只是他才刚有动作,全身上下就传来蚀骨一般的剧痛,尤其是胸口的位置,好似刀搅一般,疼的他冷汗直流,刚刚还有些红润的薄唇此时也是苍白一片。
可能是太疼了,他几乎是下意识去捂自己的胸口,然后就感觉到掌心湿润,还闻到了血腥味,令人非常的不适。
他低头看去,却只看到自己一手的血,雪色的里衣此时也已经被染红,格外的刺眼,清楚是伤口裂开了。
剧痛使他有些无法思考,抬头再次看向床边的小凳子,看着上面的药和纱布,他伸手去拿。
但因为实在是太疼他伸出去的手都在发抖,不知是不是失血过多他的眼前有些发晕,半个身子都已经挨在床边。
正当他即将碰到药瓶的时候,身子一个失力,眼前一晕整个人直接从床上摔了下去,手撞在凳子上,瞬间将凳子给掀翻,上面的瓷碗药瓶全掉了下来。
瓷碗砸在地面,传来清脆声响,碗碎裂,水全倒在了地上,染湿了温疏晏的头发。
而他也因为这么摔下来,疼的几乎就要晕厥过去,本身胸口的伤已经崩开,现在连其他位置的伤口也崩开了,一身里衣红了一大片,腰上缠着的纱布也是红了一片。
满身的伤,触目惊心。
温疏晏想要起来,可却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勉强起来又会摔回去,正巧就摔在地上那一滩被他弄撒的水上,顿时脸上被染了污泥。
如此窝囊的模样,让他几度要崩溃。
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废物,连最简单的爬起来都不行,他现在就是个废物。
他真恨,恨自己一次心软捡回来一只白眼狼,看他可怜就让他留在绮梦崖,教他修炼入道,还与他做了多年道侣。
结果这狼心狗肺的东西在羽翼丰满之际就是要杀他,若不是对他没有设防备,也不至于让这狼心狗肺的东西给钻了空子,才让他找了机会伙同他那从外面捡回来的情人杀自己。
他温疏晏就不曾对谁手下留情,唯二的两次心软就是留下了白眼狼,以及答应白眼狼留下他的情人。
也是他蠢,竟是一点没看出两个人早就暗度陈仓,这才着了两人的道。
要不是他先他们一步跳崖,怕是真得死在他们两人手上。
如今那两个白眼狼此时就在绮梦崖逍遥快活,而他这半月以来连动一下都费劲,手筋脚筋几乎被挑断,即使养好了伤他也是废物。
与此同时,紧闭的门被推开,门外走进来一人,手里还端着一碗药。
想是刚熬出来的,药碗上还冒着腾腾热气。
入门就看到摔在地上的人,那一身的血衣格外的刺眼,地上还有碎裂的瓷器。
他快步上去,将药碗放在一侧的桌上这才伸手去扶温疏晏。
不过因为温疏晏此时没什么力气起不来,最后只能抱着他去床上。
温疏晏感觉到身|下的不再是冰冷的地面而是换做了柔软的床铺,他缓缓抬头看向抱他的人,模样生的极好,一双凤眸中能看到他的倒影,明亮清澈。
明明只是穿着最普通的衣裳,可却也掩盖不去此人姣好的面庞。
随着他的低身,墨发垂落正巧落在温疏晏的胸口,很快就晕上了鲜血。
温疏晏的手缓缓穿过君渐行的发丝,随后轻轻拉住他胸口的衣裳,这才用着极其微弱的嗓音出声,“君子我心口疼,你帮我看看好吗?我不敢看。”说着他便又咳嗽了几声,使得他此时的模样是愈发的柔弱。
但毕竟是受了重伤,那怕他此时这两声咳嗽只是自己假意为之,还是牵扯到了身上的伤。
顿时疼意随之而来,他的脸色不由惨白,拉着君渐行衣裳的手也不由得收紧,似是在压抑身上的疼痛。
越是这般,他的模样便越发的虚弱,看得人心生怜惜。
而后他又缓缓抬头,露出他纤细的脖颈,上面只缠了些许纱布,未被缠绕的位置,肤色白皙如雪。
似是有意无意地他靠近君渐行,唇则随之缓缓扫过君渐行的喉间,仿佛蝴蝶展翅一般那么缓缓一扫,留下些许温热,最后他靠在君渐行的耳边。
呼吸有些沉,隐约间还能听到细微的低|吟|声,压抑着那些疼。
片刻后,他才出声,“君子我心口好疼,君子……”低声唤他,温热的气息就喷撒在君渐行的耳边,说话间唇瓣则时不时都会碰到,带着无尽的暧昧。
天不亡他,那两个白眼狼绝对没有想到,在他跳下山崖后就被人救了,而救他的人竟然是个天生炉鼎,若是能和此人双修必能修复他体内经脉修为。
君渐行只感觉耳边有些暖,那一声声唤他的名字似是要传入他的心口一般。
他低头去看怀中的人,道:“可是伤口又裂开了,你且等等,我去请大夫来。”
想到刚刚看到温疏晏衣裳上的血,尤其是人从床上摔下来了,想必是伤口又裂开了。
听着温疏晏如此难受的声音,他只得去请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