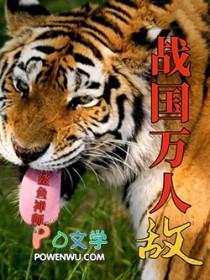葫芦小说>天气愈报 > 第63章(第1页)
第63章(第1页)
这样一份简历放在任何地方,都是耀眼夺目的存在,他根本不需要一篇天气异象的论文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搭桥铺路。
钟音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特别恨我把你从美国叫回来?”
程澍礼垂首站在灯下,诚恳地说:“没有。”
“没有。”钟音嗓音尖利地重复,“没有你让你奶奶给侯明打电话?”
程澍礼解释说:“奶奶给侯院长打电话的事情,我不知道。”
钟音心里的怒气不断上涌:“那你这次回去就交接,交接完立刻回北京来。”
程澍礼闭了下眼:“烂木等秋旱形势严峻,我暂时还不能回来。”
“还在狡辩!”钟音勃然大斥,她随手抄起桌上的一个水杯,用力狠狠掷向地面:“你就这么不想待在北京!”
听见声音,小林赶忙跑出来,看见林钰文生前吃药喝水的杯子变成了一地碎片,眼眶一红,吸着鼻子转身去拿扫帚。
看着她因为哭过而红肿的眼睛,程澍礼接过扫帚,又让她回去休息。
他仔细将地上的玻璃碎片扫起来,自始至终都情绪稳定,稳定的像是完全没有情绪。
扫完,他躬身翻出茶几底下的医药箱,找到碘酒和面前,半蹲在地上给钟音被碎片划伤的脚踝。
钟音冷眼看着他的动作,心底是极其失望的:“你待在北京待在我身边,这样我们能好好照顾你,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你是我儿子,难道我会害你吗?就非要跑到那野外,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让我跟你爸爸在家担惊受怕?”
以往说起这个问题时,钟音还算心平气和,但也基本一意孤行,坚持让他回到北京入职京大,今天是她第一次这么歇斯底里,知道沟通无用,程澍礼徒生一股无力感。
外面起了大风,寒意顺着窗户钻进客厅,温度骤降。
程澍礼走到阳台关上窗户,绕回来看了钟音一眼,态度依旧恭顺:“创可贴过期了,我出去买新的。”然后他转身走向门口。
“站住!”钟音沉下来声音,“你就站那说清楚,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程澍礼站在昏暗的玄关,背影沉寂。
隔了半晌,钟音听见他哑着声音说:“我唯独不能接受您用假病历骗我的事。”
“是我想这样?我都是因为谁!”钟音眼中含泪,怒不可遏地质问他,“为了你入职京大我花了多少功夫!你却迟迟不愿意回来,对得起我的努力吗?”
她颤抖着咆哮出声:“你怎么这么自私!”
没有反驳,程澍礼克制地点点头,说道:“妈妈,我先出门了。”
药店在离教职工楼几百米的地方,步行十分钟,但程澍礼开了车。
买完创可贴他没回家,而是将车开到京大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路上两边都是高耸的大树,树影投落下来,这里的夜色浓郁,能掩盖一切不想被人知道的情绪。
停车熄火,程澍礼抬了下手,摁掉了车灯,他一动不动靠在座椅里,从窗外的视角,只能看见他微抿的唇和紧绷的脸颊线条。
北京初秋的夜晚,空气里有了肃杀冷清的味道,冷冽狂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洋洋洒洒地飞舞在半空。
程澍礼茫然地看着那些落叶,脑中回想钟音最后说的那句话。
回望过去钟音对他的苛刻教育,不止一次地说过程澍礼自私。
小时候因为没有把喜欢的玩具送给堂弟,被她说自私,因为偷吃一块糖果,被说自私,上学考试没有达到钟音的要求,被说自私,接着长大之后,他想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也会被骂自私。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程澍礼都特别矛盾。
想自由但是不能肆意,被规训了又不甘心,就像他被钟音用伪造的病历逼回北京,又抓住帮扶的机会逃到贵州。
当极度的理性无法压制杂念,思绪乱到超出掌控,他一度觉得自己是精神出了问题。
所以在棋山看见棠又又的第一眼,除了怀疑,还有难以言说的解脱。
想到棠又又,程澍礼胸口的积郁似乎消去一点点,内心深处活了一点点,而后在深夜中,他轻轻笑了一声。
阿尧下午发过消息,说已经在吊脚楼里点了线香。这是临走时,程澍礼拜托他的,每天抽空去喂下一二三四五六和大顺,顺便在吊脚楼里点一根线香,理由是净化空气。
他准备了很多可乐和糖果,藏在只有他和棠又又知道的地方,足够她这段时间享用。
调节完情绪,程澍礼双手捂脸用力搓了搓,随后打开手机查看雨水感应软件,上面显示从六点之后传感器一直监测到有雨水。
他一直盯着电子屏幕,看了很长时间,微光反在脸上,照出眸底的平静专注,程澍礼手指点点屏幕,没忍住淡笑了下。
像是透过那些冰冷的数据看见了一个活泼的棠又又。
坐了会儿,程开济的信息发过来:“你妈妈睡了。”
程澍礼眼色一凝,他深呼吸了下,又缓了两秒,驱车驶离深夜的街道。
第三十场雨
程澍礼回家时,程开济坐在沙发上等他,正戴着眼镜看什么东西,听见门开的声音,他抻头望了望:“回来了。”
程澍礼应了一声,然后关门换好鞋,走到茶几对面坐下,知道程开济有话要说。
程开济坐到沙发上,将泡好的茶倒了一杯给程澍礼:“来。”
“谢谢爸。”程澍礼双手接过茶盏。
“跟你妈吵架了?”程开济一进家门,就敏锐地察觉到异常,从来都要在晚上钻研疑难病例的钟主任,今天竟然早早地就去睡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