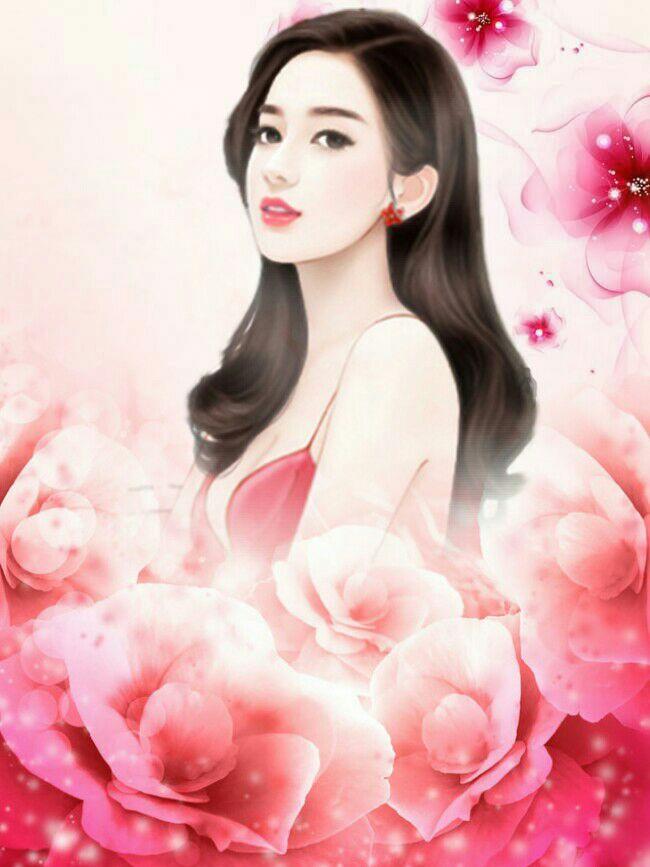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嫁给总裁不好玩+番外 > 第320章(第1页)
第320章(第1页)
家瑞把头趴在她肩膀上撒娇,轻声道:“我明天有个早会,等过俩天放假我再回来,和您好好说话。”
白母拗不过她,又体谅这里离她上班的地方远,也不再说什么,吩咐了几句才让她走。
待人走后,家里一下静了下来,她脸上的笑容便淡了,看了眼刚收拾好从洗手间出来的谨言。
“我有话问你,你过来。”她招了招手,脸色是难得严肃。
谨言看了她一眼,心里明白她大概要说些什么,抿了抿唇,走上前,在白母旁边坐下。
看着谨言已经明显大腹便便的小腹,她心里叹气,又不免心疼,再想到那人,又是摇了摇头,觉得他们之间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的,这时候怎么说都不太合适,良久低声问:“他……对你怎么样?”这是她最担心的问题。
谨言也说不上个所以然,一时不想让白母担心,还是说:“挺好的。”
白母可疑地打量了她一眼,想了想,又问:“他平时会不会经常朝你发脾气?”
谨言摇头:“……没有,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很算有机会起争执。”
白母这才想到这一层,俩人经济经基础地位不同,期间又浪费了不少的时间,算起来确实是没有多少时间一直相处,这更让她感到担心:“那你和他在一起相处起来自在吗?他会不会把在外面受的气带到家里来?”
谨言垂下眼睑,点了点头,想了想,回答白母下个问题:
“……不会,他也很少在家里谈工作的事情。”除了手机时不时的响。
白母却仍是不放心,又追问道:“那他现在每天都忙什么?”
听说没有继续担任管事一职,那总有其它的事情需要做吧。
谨言又再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自从他卸任后,俩人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每次都吵得不欢而散,哪里有机会聊到这些事情?但这俩日来看,又觉得他虽是看上去肩上的担子下来了,却还是有在关心事情,她又想,也许仍是在忙着集团的事情。
问到这里,白母忽然不知道还要再问什么,低低叹息一声,竟比之前没有见过人还要感到不安。
谨言几乎能明白白母这种担忧不安的心情,心中羞愧,说:“妈,你不要担心,他对我挺好的,真的。”
白母看了眼她的肚子,又是低低叹息了一声。
白母看着谨言的样子,只说:“他那人本来就出身比人好,家里的环境也是少有的好,他心高气傲也是天经地义,因为不用理会任何人,承人的情,只要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成了。虽说今时不同往日,他家里出了那样的事,现在又在低谷,可很多事情都不能看表面,不能拿这会儿的情况来定义以后,他这人,看上去性子怕是个不受羁绊的,也由不得人说一句,若是以后真在一起生活了,你要想清楚这一层。”
谨言微怔,很快恍然大悟,白母的意思是顾又廷从来处于优异的环境,现在突然落到这个高度,虽是比下有余,却已是他三十多个年头来的最低潮时期,所以也许会因为这样一个时刻而勉强放下身端,待来日东山再起,他只会又恢复成本身的自己,因为那也才是真正的他,现在会隐忍,也不过是一时的。
一天成了鳏夫,但不会永远是鳏夫。
白母感叹,“你从小就听话懂事,我一直以为你会找个同样稳当温和的人……”
从白母说话的语气看,似乎是对顾又廷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她也知道,白母难免会担心她,谨言压低了声音说:“妈,我知道,但他今天会这样其实……和老太太的事情有关系,他可能一时没法适应,多点时间也许就好了。”
白母前晚也听到她提及一些顾老夫人的事情,一时嘘唏,也不再说话。
谨言心里想着事情,一夜没睡好,早上睁开眼发了会呆,就从床上起来了。
……
同样一夜没睡何止是她。
顾又廷回到凤凰路,想起周云哲说起的项目,立刻拨了个电话过去,却是没人接,他再打,问人是怎么回事,那边嘟囔着说是这项目不批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他在云城的时候就开始提审了,有许多人都帮忙着打马虎眼,只有那一位还坚持已见,这不,这几日被人扰得无法只能关了机。
顾又廷立在原地站了好一会,他一直在想,那个项目之前也了解过,但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呢?
听周云哲话里的意思,看来是着急了。只是他现在没必要为了一个项目去做擦边的事情,钱财吃几辈子吃不完,说大不大的项目批下来,如果被上面的人盯住了,如果有人寻心要找他麻烦,只要花些时间查他,再找个借由,他还想着能侥幸躲过?
到底是为了什么?
顾又廷想了一整晚,都想不出这件事情的蛛丝马迹,不过是个普通的项目,一条普通的临海大桥。
这个项目不行就换了另外一个项目,像这样利润的项目并不难得,可听周云哲的语气是不会轻易罢休。
他怎么想也想不出周云哲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烦燥地抓了抓把额前的碎发,劲道有些大,忽然扯到伤口,他看着手掌包着的纱布,有些发怔,想起晚上在别墅里,面对趾高气扬,目光不屑一顾,嘴角噙着一丝嘲弄的周云哲,一股悲愤之气,从他的心间涌到喉头从嘴角的缝隙溢了出来,他眼睁睁看着他从面前离开,忍着一言不发,身旁的女人把手紧紧按在他这只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