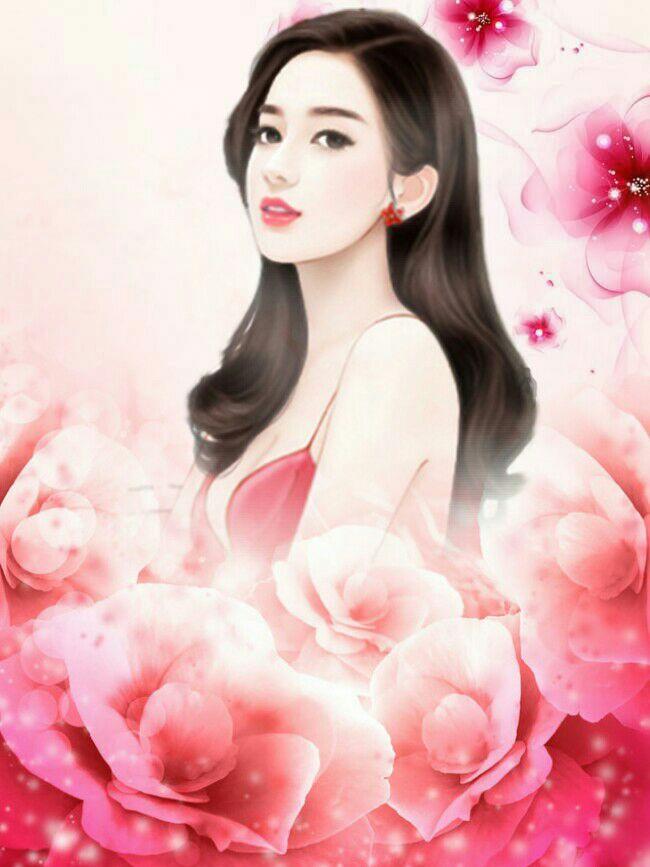葫芦小说>七零边疆二婚妻 > 第400章(第1页)
第400章(第1页)
“怎么,当初你到北京,给我们兄弟压著打的事儿,现在应该忘瞭吧?”仇天海拿胳膊肘子碰瞭碰聂工,就说。
聂工没说话。
但二蛋和聂卫民的脸随即就黑瞭“叔叔,你居然打过我爸爸?”
“小时候你爸耸著呢,特好欺负,真的,胆小的不得瞭。”仇天海左看右看看,感慨说“没想到你生瞭这么多儿子,我隻能说,你和转男呀,真能生。”
然后,他又拍瞭拍胸脯,说“哥现在不是当年啦,想起当初老打你,心裡真过意不去。哥现在在北京混的是真不错,有小汽车开,在东方饭店还有长期包房,那可是你拿著介绍票都住不来的,咋样,哥今天带你好好儿享受享受,开开眼,也算赔当年的罪,咋样?”
聂工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是来陪傢属学习的,我们有地儿住。”
仇天海哪能放瞭他啊“你们这些生活在沙漠裡的人,偶尔上趟北京,那就跟开天眼似的,啥没见过的都该见一见,没享受过的都该享受享受,我得告诉你,北京跟别的地儿可不同,没个人带著,我还怕你迷路呢。”
拉拉扯扯,一路下瞭火车。
仇天海也不知道做多大生意,反正那隻小皮包瘪的呀,说它裡面就一张纸陈丽娜都信。
而聂工一傢呢,大包小包,三个孩子一人手中就是一隻旅行箱。
“转男啊!”仇天海跟聂工搭不上话,转而来找陈丽娜瞭,结果,话刚一出口,陈丽娜就来瞭一句“大哥这眼睛不合适啊,孙工去瞭多少年瞭你不知道,你要去过矿区,你就该看到,招待所关于矿区的简介裡,就有她和六个科学傢一起牺牲的事迹瞭,您故意这样,好吗?”
“新嫂子挺能说啊。”仇天海的笑凝在脸上瞭。
聂卫民说“我妈是乌玛依毛纺厂的书记,你要的的确凉啊,归她管。”
仇天海愣在当场,恨不能搧自己一耳刮子。
北京西站的出站口,那叫一个人流涌动。
“哎哟喂,原来您就是陈书记,陈书记您好您好!”仇天海拨著人,撞著人,还在那儿喊呢“那我更得招待你们瞭啊,我得告诉你们,我有司机,车就搁火车站外停著呢,咱们一上车,先上东方饭店搓一顿,然后我再带你们去开住宿票,咋样?你们外地人不知道我们北京的事儿,要住店,那得先开票,就开票那地儿,你们都找不著我告诉你。”
是,火车西站外停著好几辆小汽车呢。
不过,最耀眼的一辆,是一辆斩新的上海牌小汽车,一三十出头的中年男人,驼色呢子大衣,戴著墨镜,就在车前站著呢。
一见聂工全傢出来,上前就来提聂卫民的行李“好小子,长这么大啦?”
仇天海嘴巴直接张瞭个大“哎哟,郭总编,咋是您啊,我怎么就这么荣幸,把您给碰上瞭?”
这是《新青报》的总编郭滨,真正根红苗正出身好,还自已争气的有为青年,当然瞭,在北京城裡也小有名气呢。
仇天海平时找都找不见的人,给聂卫民提包呢。
他的嘴巴呀,张的更大啦。
“接个朋友,我小老弟,聂卫民。”郭滨拍瞭拍聂卫民的肩膀,说“几年没见,小伙子长这么高瞭。”
“陈场长,我带你们去的地儿,其实就是我的房子,不过我和我傢属不住那儿,而且吧,那地方离党校挺近的,你不托我给你租房子嘛,我就寻思著,你直接住过去就行瞭。
毕竟水电暖都齐全,你要想开火,啥都方便,我这个房东也不会东打听西打听,你说是不是?”郭滨上瞭车,就说。
这就对瞭,陈丽娜来之前,委托郭滨给自己租间房。
因为别人可以住党校的宾馆,她不能,她怕妹妹哭闹要影响别人学习呀。
“那房租,等我打听好价格瞭给你付,你看成吗?”
“成,怎么不成。”车一拐,直接就进居民区瞭。
一室一厅的房子,厨房裡有锅碗瓢盆,厕所裡是蹲坑儿,不过郭滨特地进来提醒“这厕所隻能洗衣服,上厕所得去外面公厕裡,早晚那有痰盂,得你们自己端著倒。”
好吧,二蛋又把裤子提回去瞭。
“北京人民过的真艰苦。”他说“哥,我在这儿连屁股都转不开,咱要在这儿生活一个月?”
三蛋这不正给妹妹换尿佈呢嘛,就说“反正我不管,卧室是属于我和妹妹的。”
妹妹也觉得新奇瞭,蹬著两条小腿,在大大的床上四处转著脑袋,看来看去。
聂卫民一个猛扑趴到床上,装大老虎吓唬瞭妹妹一下,见妹妹笑瞭,秒变小狗“汪,汪汪!”
妹妹咧开嘴,笑的愈发开心啦。
要说聂卫民三兄弟现在最爱什么,想都不用想,那绝对是妹妹。
就那么小小一个人,奇瞭怪的,咋就那么好玩呢。
聂工一傢愉快而又繁忙的北京生活,就这么开始啦!
收房子啦
“想要房子,那没门儿,官司早打完瞭,房子也归我瞭,有我在,这房子是就是我的,我要死瞭,这房子那就是你们兄弟的,有他聂老大啥事儿?”
老太太乔慧正在打肉馅儿包饺子呢。
给肉馅裡加瞭点儿水,继续打,她说“他又不是乔淑亲生的,能叫乔淑养大成人就不错瞭,还想要我们傢的院子,我们老乔傢多少姐妹都不够分,他想得美。”
仇天海说“要他原来的旧媳妇儿,这事儿怕还好说,新的那个,我看著精明著呢,隻看眼睛,就是个难缠的。”
乔慧笑瞭笑“再难缠,北京城也不是她撒野的地方,怎么,聂老大是专门跑来要咱的院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