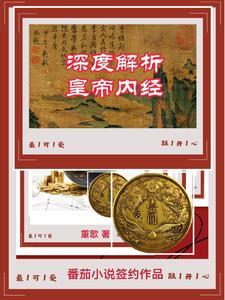葫芦小说>囚妃传 > 第二百三十五章 恐吓信(第1页)
第二百三十五章 恐吓信(第1页)
砚林想找刘大人的时候,刘大人也正想找砚林。
他仍旧坐在衙门公堂下的石头台阶上,托着腮,头仰望着天。他在等,看那样子像是在等久不见了的情人。
“大人!”砚林从一边偏门进来,快步走到他面前,行礼,“大人,您找我?”
“林捕头!”刘大人见到砚林,猛地坐了起来,不,他是从石头台阶上弹起来的,双手抓着砚林的胳膊,“林捕头快请起,快请起,你听我说啊……”
“大人!”砚林打断他的话,一脸愧疚,“大人,是属下办事不力,至今未查出丝毫线索。”砚林这么说着,人虽低着头,但目光看着刘大人,观察着他的举动。
“不不不,林捕头,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刘大人忽然变得客气又神秘起来,拉着砚林的手,把他向公堂上拉。
砚林由着他,跟着他走,看他有什么花招。却不想,他走到公堂的审案桌上,翻了翻,找出一张不大不小的纸来,递给他。
狗官,十日之内,必取你的狗命!
砚林一怔,抬起头,“大人,这是威胁恐吓信?”
“林捕头,你得救救本官啊!”刘大人好象快哭了,那架式像是随时都可以给砚林跪下似的,“看看,看看,这些刁民!本官自打被逼……不,是自打走马上任,可也没干过什么对不起黎民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事啊,怎么就被狗官了?还要取我的狗……我的命!”
刘大人
这个委屈,这个冤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捶胸顿足,懊悔不已。
“大人,先别急,我……”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刘大人扯着砚林的衣袖,不像是审案的大人,倒像是蒙冤诉苦上告的苦主,“林捕头,你可得救我,为我做主啊,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啊!”
“大人,大人……”砚林本是怀着一腔仇恨和疑惑,前来这里与他斗智斗勇的,此刻却被他哭得不知所措了,“大人,你你先冷静点……哎,先别哭了!”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出去躲躲啊?”
“大人?”砚林不解,“您在任上,怎么可以说走就走。”
“可是,这威胁信都送到我衙门里来了,我不走,难道留着等你来取我够……我的命啊?”
“大人,别急!”砚林没办法,只得扶刘大人坐到旁边师爷的位置上,“这现在只是一封信而已,您在这里不还是好好的吗?”
“这我怎么好好的?他可说十日之内必取我的够……我的命啊!”刘大人提心吊胆,“你说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还睡得着觉嘛我?”
“大人,别急,不是十日吗,我们趁着这十日的期限,找出这个威胁者是谁,将他关进监牢,不也就没事了吗?”砚林甚至像在哄小孩,生死威胁的确是大事,但也不至于像他这样一惊一乍的。砚林摇摇头,“大人,您向说说看,这信是什么时
候看到的,谁送来的?”
“知道有人送来我早关起来审了。”刘大人垂头丧气,目光中充满着惊恐,指了指门口,“自己看吧。”
砚林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才自己走过去。大门是木头的,年久失修,也旧了糟了,上面有几个刀刻划痕,想必是哪次不小心的打斗所致。但不太起眼的地方,有一个新的箭孔,想必是从远处射过来的。砚林再低头看看手里的信,“大人,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早上。”刘大人快被打垮了的样子,指着门,“连那个地方都能射得到,那射到我脑袋上,岂不容易的很。”
砚林笑了,“大人,您放心,若是他射到您脑袋都容易的很,就不会寄这信这么麻烦了。”
“说得也有道理,可是我这心里还是犯嘀咕啊。”
“那么大人,这信您还给什么人看过了?”
“没有。”刘大人摇摇头,“只有你一个。”
“大人,放心,这几日,您照常做事……”砚林本是这么说,但旋即一想,若是刘大人是被冤枉无辜的,他这么告诉他,万一十日之内一哪天真的被一箭射死了,他岂不罪过大了,也落了个保护不力的罪名?“大人,这样吧,这几日,您就在家好生歇着,将门户关好,除了我,也暂时别告诉别人了,连咱们衙门内的其他捕快,您也别说,知道么?”
“当然,当然。”刘大人抓着砚林的胳膊,手都是颤抖
着的,“林捕头啊,林捕头,我现在可就靠你了啊!”
“大人放心,我一定尽快查出这是谁做的。”砚林说完又笑了,“还有啊,大人,或许,不是什么杀手要杀您,只是有百姓对您恶作剧呢,也说不定。”
“什什么人对我耍这样的恶作剧?”刘大人反而瞪大了眼睛,“刁民,实在是刁民。”
“好了,大人!”砚林冷冷地说,“您不当官的时候,或许被的官也骂您是刁民,您也骂官是狗官了。”
“你……”刘大人被砚林这么一顿呛,刚要发作,一想到他自己的小命还抓在人家手里等着救了,也就唯唯诺诺的不敢吱声了。
“那,林捕头,您这有什么打算呢?”
“没有啊。”砚林实话实说,说完一见刘大人一脸阴沉沉的,又害怕又紧张又气的样子,心里一阵烦乱,这人若是真的伪装,那也真是演技太好,可以唱戏了。可不若真是被逼无奈,做下这么多坏事,他也真是难以想象。一时他实在是不敢误判,“行行,您先别着急,我到对面去看看,咱们这个地方,这么蹊跷,也隐蔽,他直接射到这里,恐怕也必须有一个角度才对。我先到对面去找找,或许能找到立足点,再去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那一代徘徊过。”
“高,是高的地方!”刘大人神经质地提醒他,他不可能是傻子,这角度只能是从高处向下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