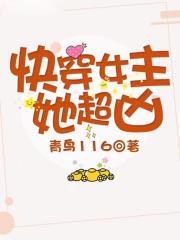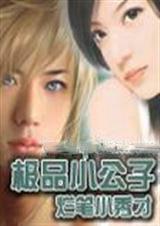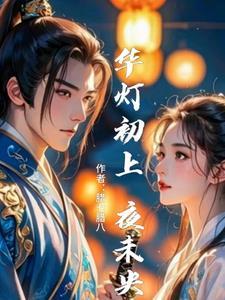葫芦小说>穿越到安史之乱当医生李明夷卢小妹 > 第261章(第1页)
第261章(第1页)
话还没说完,只听锁链哗地一响,李明夷手里那袋菱锌矿已经叫青年抢了过去。
那张汗泥俱下的面庞咬牙切齿挤出一个笑容:“军机不待。”
不必再念了!
他用眼神凶巴巴地补了一句,转身钻进营帐里。紧接着,便听见一阵噼里啪啦怒气冲冲的翻动声。
赵良行心疼叫他拿来撒气的药炉,匆匆和李明夷交代了安置的地点,便赶紧跟进去亲自看着。
“你还真有办法。”谢照往门框上一靠,往里转了转眼珠,不乏打趣地笑道,“我果真是多余留这半日了。”
对方只道:“还未多谢小谢郎为我奔走。”
这话放在别人身上或许多少带点含沙射影的意味,可这人说出口的绝对是真心之言。谢照站直了背脊,想了想才开口:“他们并非针对你一人,朔方军军风本就剽悍——有时规矩太多,反而会束手束脚。”
这点李明夷倒不否认:“太守规矩,狼就养成狗了。”
见他一身干净,显而也没吃到亏,谢照放下腰刀,会意一笑:“你还不知道吧?以往大家都喊他们西北蛮子,这股野人做派,便是郭公也头疼了许久。”
可若真抹平利爪、摘去獠牙,又将以何驱狼逐寇?
看郭二郎在军营中的威望,便知郭子仪本人在将士们心中地位多高。这是数场指挥得力的血战换来的拥护,当然不会轻易复刻在一个有叛国之嫌的军医身上。
谢照想宽慰他的道理,李明夷并非不能通达。既然是以本事说话,郭二郎的为难倒也算给了他一个机会。
他不置可否地颔首:“不管蛮子还是野人,能打仗的才是好兵。”
对方回答得如此阔达,谢照不觉哑然。
他抬眸看向身前连营的军帐,目光在背后隐约亮起的炉火中明晦交加:“本不该把你卷进来的,只是此次收复长安事关机要,郭公万事筹谋,只恐一疏。”
此次收复长安,既是郭子仪首次独挑大梁,也是朝廷最后一次证明自身的机会,任何人都输不起这一仗。
李明夷同意地点头:“这一战必须赢。”
谢照的视线慢慢回转,落在那张处变不惊的面庞上。
一年未见,可想彼此都经历几多变故,可悲难未曾磨砺其锋芒,倒更令他心性坚韧刚强。
他动了动唇,终是轻轻出声:“郎君以前可不是好管闲事之人。”
非要说的话,对方也只对疾病与病患抱以兴趣和感情,身外之事似乎都不能打动他分毫。此番虽然和郭二郎起了冲突,可以谢照的了解,这已经算这人相当配合的姿态了。
徐徐夜风鼓动在两人之间,无形之中将久别的陌生与距离填满。李明夷抬眸看着这位也将远行的老朋友,认真说道:“对我来说,不是闲事。”
国不将国,何以为家?
这个简单的道理,已经有无数人用血肉向他证明。
谢照眉宇间也不乏动容:“是啊。”
感叹之语还未说出口,便听对方直接以冷静的口吻打断:“我的器械很可能还在洛阳行宫。”
谢照喉咙滚了滚,一时忘了刚才想说什么。
夜色茫茫,李明夷不作伪的思忖却都写在脸上。
想要以合法的手段取回自己的所有物,最简便也最正当的途径就是从军,以军功换取收缴的物品。按唐军的战术不难推断——收复长安之后,便是洛阳。
所谓声名,他本不在意,更不需要。
还是实实在在的回报更值得他付出心力。
谢照怔在原地,竟是半晌才明白过来他这句直言不讳的话,不由摇头而笑。
他也省去准备好的一番口舌,将刀挂在腰上:“我要走了。”
李明夷猜度:“你去凤翔?”
谢照错开他投来的视线,未答这话,径直往前迈步。直至擦身而过,才举起手臂和他晃了晃:“下次再见,希望还是活着的李郎。”
李明夷顺着吹鼓的大风往后看去,扑朔声中,那道缁衣带刀的背影很快被重重军帐吞没。
必当再见,他用目光无声地回应道。
*
营帐之中,眨眼两个时辰。
“都是按你要求做的,现在满意了吧?”
顶着一对大黑眼圈的青年,捧着新鲜出炉的几碗炉甘石粉,浑然已经被磨光了脾气,只想赶紧交差。
李明夷接过他辛苦半夜的成品,用手指蘸取碗里被炙烤后研磨成粉的细细晶粒,放在灯下仔细检查。
本还有些发青发白的矿石已经完全被炙烤为粉红色,又被研磨成细如尘埃的粉尘。对方抱怨虽多,做事倒还算利落踏实。
虽然远不能和现代工艺下的纯净度相比,但经过细微的化学变化,这些小小的矿石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另一种更加具有医疗价值的物质。
“这是炉甘石?”
已经有些老态的赵良行也尽职尽责地陪了一宿,直至此刻才提出自己的疑问:“古书有云,炉甘石收敛肌肤,可用于疮症,只是不知郎君为何要炙烤再用?”
一听军医长口中这话,青年先是惊讶了一瞬,随即竖起眉毛:“你玩我呢?”
灯下之人眉目舒展,倒是不为触怒,反问:“阁下何出此言?”
青年噔一声撂下陌刀,忿忿席地坐下,知道这人厉害之处,不敢把话说得太死,只嘀咕着抱怨:“赵公说古书有记载,想必真是药石。既是药石,何不往药市里采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