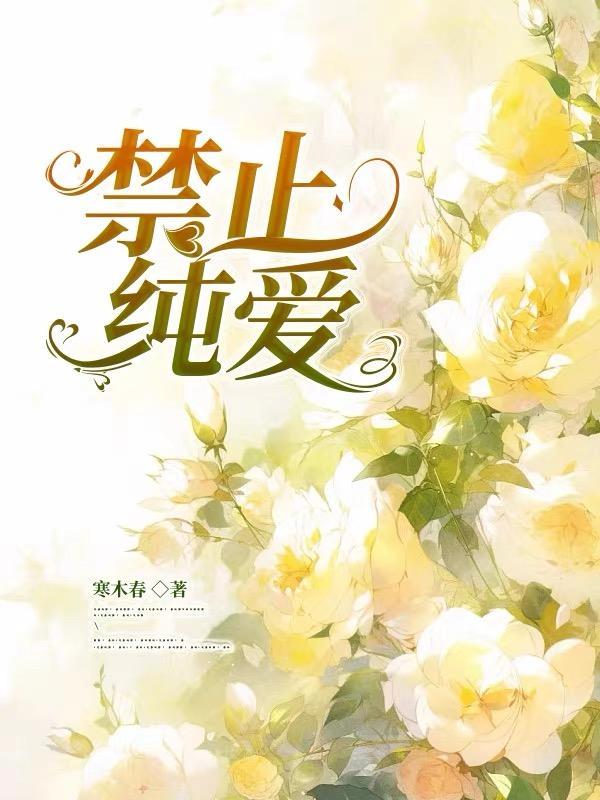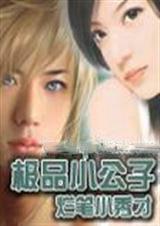葫芦小说>穿越到安史之乱当医生李明夷卢小妹 > 第178章(第1页)
第178章(第1页)
“凭感觉吧。”李明夷这才回答谢望的问题。
“感觉?”林慎有些惊讶于这是李明夷能说出的话。
但很快,他便明白——
就像刚刚找不到正确的神经时,李明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选择向完全相反的臂内寻找,这或许也是一种感觉。
也可以称之为经验。
林慎再一次抬起眼眸,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位咫尺之内、却仿佛遥不可及的主刀医生。
这样令他们惊心动魄的手术,他到底完成过多少次?
还未等他从讶异中回神,只见对方操控着眼科剪,将被牵起的神经外层的膜剪开,接着用小型的探针将其进一步分离,把本就不算粗的神经又分为五束。
要达到解痉的治疗效果,需要切除至少百分之五十的神经纤维。
所以接下来,要剪断其中的三束。
面对这支支配着一部分手臂、重要非常的外周神经,李明夷的动作停顿下来。
在改良后的术式中,现在应该用神经电仪器分束进行测试,根据肌肉收缩情况,优先切除低阈值的分支,以此最大程度地保住病人术后的手功能。
而在现有的条件下,到这一步已经是他所能做的极限。
上天,请你再仁慈一次。
他默默地请求。
接着,在身旁两人大气也不敢出的注视中,慢慢伸出那把小巧的眼科剪。
咔的一声,他将其中的三束剪断。
第66章医学永远不是一条纯白的道路
从中切断之后,李明夷继续在其上方约一厘米的位置做了同样的切口,以保证这三束神经纤维不会再生。
这同时也意味着,这只手臂的功能将在几个月后永久地丧失一部分。
所为仅仅是决战前的振臂一呼。
不等价的置换,如同与魔鬼交易,如果是一千年后的自己知道唐朝的这场手术,一定会痛斥为中世纪的邪恶。
微型的拉钩慢慢松开,李明夷将残余的神经纤维妥善地放回原来的位置。
“正中神经部分切除完成。”
宣布完第一阶段的手术完成,李明夷规律地深呼吸几次以作休息。短暂的停顿之后,便继续深入钝性分离,在肱二头肌与肱肌之间寻找需要部分切断的第二根周围神经,肌皮神经。
这根神经倒是规规矩矩地走行在经典的解剖位置上。
看到逐渐在肌肉中被暴露出来的白色筋线,三人不由同时松了口气。李明夷重复刚才的过程,小心而仔细地进行分离、切断。
直到这时,林慎才把悬着的心放下一半,想着上半程的意外,认真请教:“方才你们说病人的神经走向和普通人不一样,那李兄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该去那个位置找的?”
“遇到过一次就知道了。”李明夷的视线专注地集中在细小的神经上面,漫不经心地回答,“手术的成功概率是例数堆积起来的。”
林慎眨了眨眼,仍看着他。
“那……”一边递出器械,他一边问出了那个好奇许久的问题,“你有失败过吗?”
话刚出口,他就有些自悔。
在手术台上问这个问题未免太不吉利。
“有过。”
出乎林慎的意料,对方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干脆而坦诚。
轻轻咔的一声,肌皮神经也被剪断了部分。李明夷耐心细致地处理着剩下的步骤,眼神没有因此有一分的动摇。
“所有手术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失败上的。”他说。
就像眼前这个曾被医学界废止的手术,最初的病人因其终生残疾。但就在短短一百年后,它在显微镜和神经电的加持下重新回到手术室中,拯救了成千上万因脑瘫而肢体痉挛的儿童。
完成世界上第一例外周神经部分切除术的医生是罪人,而完成最后一例的医生是救世主。
医学永远不是一条纯白的道路。
“如果不能从失败和死亡的阴影中走出去,是做不了医生的。”
回答完这个问题,李明夷松开持物许久,已经紧绷的双手,把位置让给自己的助手。
“缝合吧。”
比起一层一层结构规律的腹部,肌肉复杂的手臂缝合难度陡增。但对于解剖经验充足的谢望而言,这个工作应该算不上为难。
谢望也没有推辞的意思,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实践自己的练习。
虽然把缝合留给了助手,李明夷也没有就此休息,观测着患者生命体征的同时,一眨不眨地观察着谢望上下穿梭着针线的手。
和最开始不同,他看起来已经很适应持针器,缝合的手法也更接近于科学的方式。可以想象在这段分开的时间里,他独自在无人处练习了多少次。
林慎亦难得地久久沉默,只是配合着谢望给他穿线、递针,目光不时落在李明夷专注的脸上。